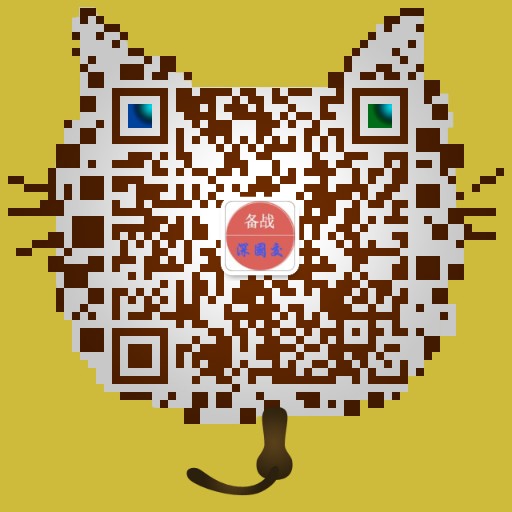当前位置:首页 » 深国交哲学社 » 正文
-

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以下缩写L'OBS): 米歇尔·福柯,你曾在《新观察家》杂志中写道,在你对伊朗的报道中,这个国家目前正在寻找一些我们西方人自文艺复兴和基督教危机以来所失去的东西。你称之为「政治精神性」(political spirituality)。[2] 这个表达让很多人感到诧异。我想你或许应该在这一点上解释一下自己。
本文《我们时代的政治精神性:福柯与《新观察家》的访谈》[1](原标题:"Political Spirituality as the Will for Alterity: An Interview with the Nouvel Observateur")译自https://www.journals.uchicago.edu/doi/abs/10.1086/711138.
作者 / Michel Foucault、《新观察家》杂志 (Sabina Vaccarino Bremner) 翻译 / 胡写 排版 / 亦源
米歇尔·福柯(以下缩写FOUCAULT): 我首先会把回应的责任推回给那些感到诧异的人。我讲一个轶事: 我在伊朗时,有一份新闻杂志(不是贵杂志)的记者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像所有关于伊朗的文章一样——以某种对于宗教运动波及全体伊朗人民的着重强调结尾。我在这篇文章发往巴黎之前读过。在巴黎印刷时,编辑们添加了「狂热」这一形容词。 那么,现在是否应该由那些试图理解伊朗正在发生什么的人来宣布这种宗教或精神性运动的存在,来为他们自己所辩解呢?难道不应该是那些以这种敌意回应的人来解释他们为何如此抵触我的表达吗?
L'OBS: 好,我们是该考虑双方的立场。但从你的角度来看,当你使用「政治精神性」这个表达时,它在我们的传统和观念中充斥着许多含义——尤其是「精神性」一词。你能解释一下你的意思吗?这个表达仅仅是描述性的吗?
FOUCAULT: 我试图找出在过去与现在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能够让整个人口,这些人手无寸铁的人们,去对抗一个可怕的、恐怖的政权——一个无比强大,有着军队和绝对庞大警力的政权。我不知道人们是不是把武器藏到了哪里,但如果有,他们藏得很好,而且数量不多,因为尽管每天都有几十人死亡,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拿起武器。 那么,是什么力量使人们每天都不断重燃如此顽强、执着的反抗意志,并主动接受牺牲,甚至是愿意接受自己为之献身的牺牲?显然,我们不应该在像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寻找这种力量,也不应该在西方意义上的某种革命意识形态中寻找,我们应该另寻他处。
L'OBS: 或好或坏,欧洲解释伊朗危机的主流假设是国家现代化速度过快。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些先验 (transcendental) 的解释来包装 (truss up) 一现实呢?
FOUCAULT: 第一,这不是包装;第二,它们完全不是先验的!存在的是现实。人们完全可以说:「我们不想要现代化;这个政权所强加的发展节奏和政治结构我们再也忍不了了;我们拒绝为强加给我们的现代化付出如此代价。」但人们不是这么说的。 首先,现代化的问题。我认为——顺便说一下,我觉得最近几周在土耳其发生的事情也证明了这一点——今天在伊朗被抵抗的不是现代化,而是陈旧化 (antiquation)。[3] 这种陈旧化是「凯末尔主义」,即某种类型的穆斯林、伊斯兰和其他社会的重组模式,这或多或少借鉴了西方,并在20世纪20年代由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发展起来。[4] 巴列维王朝一直遵循这种模式——明确地推行到1938年或1940年,随后默默地继续推行它。

默罕默德·礼萨·巴列维(1919-1980) 此外,事实是,在最广泛的阶层里——也就是说,从知识分子到阿巴丹的工人,从德黑兰的商贩 (Bazaari) 到偏远伊朗东部的农民——大家确实都认同像霍梅尼这样的宗教领袖。[5] 他们真正认同的是伊斯兰,是另一种生活方式,它并不是与现代相对的老旧的生活方式,而是一种与宗教联系的,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 我认为事实就是如此;你无法否认,我也不认识许多从伊朗回来后会否认这一点的人。因此,问题在我看来,是要弄清楚他们是否只是在自欺欺人;是否仅仅是是人们以为自己抓住了某些宗教价值,而实际上只是在用他们仅剩的词汇来解释对当前局势的不安 (malaise)。
L'OBS: 你认为你在伊朗观察到的现象是一个可以推而广之,应用到当下现实中的某种概括性假说吗——即在特定情况下,宗教正在变成反抗国家及其代表的异议空间 (dissident space)?
FOUCAULT: 这是个好问题,这让我能在此引入一个概念区分,它对我来说相对清晰,但恐怕我还没有向读者充分澄清。当我谈论精神性时,我并不是在谈论宗教;也就是说,精神性和宗教需要适当的区分。让我感到无比惊讶的是,在人们的心中,精神性、通灵论 (spiritualism) 和宗教竟然被混为一谈,变成了一个混乱不堪、无法分辨的含混体![6] 精神性可以在宗教中找到,但也可以在宗教之外找到;它可以在佛教这种无神学体系的宗教中,在一神教中,甚至可以在希腊文明中找到。[7] 因此,精神性并不是必然地与宗教绑定,尽管大多数宗教都包含着精神性的维度。[8] 那么,什么是精神性呢?我认为它是一种实践,通过这种实践,个体被移置 (displaced)、被转化 (transformed)、被扰乱,以至于放弃了他们自己的个体性 (individuality),放弃了他们自己的主体位置。这已经不再是之前那个主体,一个与政治权力相关的主体,而是一个特定知识模式、特定体验或信仰的主体。[9] 在我看来,能够从政治权力、宗教权力、教条、信仰、习惯、社会结构等为你所框定的主体位置中挣脱出来——这就是精神性,也就是成为一个不同于自我的存在 (autre que soi-même)。无疑,宗教既是这些精神性形式、精神性实践的避风港,也是它们的限制。宗教规定了人们该如何成为不同的自己,应该走向何处,应该成为何人,等等。实际上,宗教为精神性建立了一套既定的编码 (codification)。[10]
L'OBS: 所以你强调的是,尽管伊朗的什叶派如今成为了一种反抗国家都异议空间,但也限制了其本身。
FOUCAULT: 如果不是起源于一种精神性的运动,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革都不会发生。 看看中世纪末期发生的事情。毕竟,在中世纪与十六世纪末之间曾发生过许多震动欧洲的运动,这些运动至少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之间被称为「革命时期」(所发生的运动)同样重要——如果不更为重要的话。信仰、生活方式、社会关系、政治服从形式、社会等级制度、经济实践——一切都改变了。现在几乎可以确定——历史学家已经证明了——十五、十六世纪的这场运动不仅发生在宗教内部,而是发生在一种扰乱了宗教本身等级结构的精神性运动中。它是宗教对宗教的对抗! 无论是十五世纪弗拉芒的禁欲主义运动,还是德国同时期或紧随路德之后发展起来的各路宗教团体(比如再洗礼派运动),还是在十七世纪英国宗教团体的巨大扩散最终瓦解了君主制机器 (Appareil) 并推动欧洲历史上第一次革命的发生——所有这些,我认为,都证明了精神性可以完全被视为所有伟大的政治和文化变革的根源,证明了宗教在精神性的运动中可以发挥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这种运动本身是精神性的,而不是宗教的。[11] 这才是我所指的。
L'OBS: 你知道我们大学所使用的老生常谈的理论框架,它们传统上将那些促使个人起来反抗压迫他们的力量视为一种泡沫、上层建筑;简而言之,在这一套的解释中它从未被视为一个不可约化 (irreducible) 的根源现象。 我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学习十字军东征,我要为此写一篇论文。如果我在论文里解释说,那位离开讷韦尔前往耶路撒冷的十字军骑士是为了解放基督的圣墓,我肯定会被打一个低分。如果我说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当时正值西方人口爆炸,他无以为生——换句话说,如果我解释说他去到那里是为了西方的产能过剩而扩展市场和机会,那么我的解释大概会受到欢迎。
FOUCAULT: 或许应该问,你的教授是不是应该被打低分! 我认为历史学家们养成了一个坏习惯,他们只承认某些非常精确和确定的因素之间的因果性。对于任何从不符合这一(从古典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所借鉴的)蓝图对所有关系阶层化的分析,他们都完全拒绝。但这不是重点。并不是说你提到的因素不存在。相反,问题在于,面对如此的孤独、贫困、被排除在曾经赖以为生的社会网络或社会整体之外时,他会产生何种的反应,等等。 这才是问题所在:是何种的回应。原因 (Stimulus) 的性质永远无法解释对其所作出的反应的具体性质。这些原因——贫困、作为家庭中最小成员、封建结构,等等——所有这些事实,这些导致了一定数量的个体在中世纪社会中变得或不可欲 (undesirable),或不可用 (unusable),或流离失所,但这些都永远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真的发动了十字军东征,真的相信了解放圣墓对他们自己和基督教全体无比重要。
L'OBS: 原因的性质永远不会决定回应的性质。
FOUCAULT: 我要说的是,伊朗人民在强加给他们的经济状况下受到的苦难,屈服于警察政权毫无人道的压迫,看到他们的自然财富在自己的眼前既被掌权者和美国人共同「掠夺」——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毫无疑问,目前只有伊斯兰信仰能够真正将精神性赋予这种意志——也就是说,一种成为与自己不同的存在的意志——一种能被组织成一种政治运动的具体、明确形式的意志。[12]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 L'OBS: 你在伊朗观察到的现象是否对其他当代现象也适用?
FOUCAULT: 我认为是的。毕竟,没有精神性的革命是例外。
L'OBS: 你能举几个例子吗?
FOUCAULT: 也许法国大革命;我会说这是唯一一次特别的革命,人们想要成为与之前不同的自己,想要不再成为任何意义上的主体,但在这次革命中,人们为其辩护的解释、运动的展开方式,都没有借用任何传统的精神性坐标。
L'OBS: 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反而是一种断裂。
FOUCAULT: 这次革命是立法者可以真正建立起一个完美与透明秩序的社会重组。这是唯一一次人们认为通过一个良好的议会代表制度可以解决问题的革命,认为通过充分的智识与哲学反思能真的使人们不再成为他们原来那样的主体,从而转变成普遍理性 (universal reason) 的主体,等等。
L'OBS: 这与英国或美国革命相反。
FOUCAULT: 十六世纪的那些危机依然是精神性的。[13] 看看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为1917年革命铺平道路的所有东西难道在根本上不正是一种精神性运动吗?革命的现象由一股巨大浪潮般的热情所带来,而后又被布尔什维克所领导。从根本上来说它难道不正是我所说的,一种深刻的精神性的运动吗?我是说,这一运动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希望现状或事实发生改变,而是知道如果不改变自己,就无法改变现状。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处于革命意志核心的正是这种「成为不同的存在 (autre que ce qu 'on est)」。
L'OBS: 现在我想我们可以谈一谈……
FOUCAULT: 如果你允许,我还想补充一些东西。 拉博特 (Rabaut Saint-Étienne) 有一句名言我想可能很好地概括了我想说的内容。拉博特说:「人必须被改变,世界必须被改变,思想必须被改变,言辞必须被改变,一切都必须被改变……一切都必须被摧毁与重建。」[14] 这句话的第一部分,是真正精神性的:改变一切,首先是改变自己,成为不同的存在,同时根本不知道那将会是何种不同的存在——这是一种为自身寻求异质性 (alterity) 的激进意志。[15] 接着,当拉博特说:「一切都必须被摧毁欲重建」时,他指的是一种与过去所有的制度彻底决裂,并在理性体系的基础上重建这些制度的哲学意识。这句话的第一部分,是精神性的层面;第二部分,是哲学革命的层面,而后者必须由前者开启。法国大革命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认识到自身精神性的革命。[16]
L'OBS: 就伊朗的情况而言,这种寻求异质性,不再成为现存主体的意志,通过重新投入到那些最容易获得,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宗教实践和怀旧中得到了实现。就此而言,你如何解释这种回归旧有实践的现象呢?例如,霍梅尼能够煽动人们摧毁电影院,拒绝西方化,回归某种非常接近传统神权政治的状态——这如何能够被描述为某种可能的异质性?[17] 或许我表达得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在文明进程中这种最倒退回的最为古代的实践可以被视为一种可能性?虽然我想你其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FOUCAULT: 这一精神性的运动在于利用其手头的工具;问题不在于工具是否是宗教性的,而是知道这些工具在与这种(寻求异质性的)意志的联系中产生的意义是什么。
L'OBS: 你如何解释你提到的那个报纸记者的报道中提到的反应,以及对你自己的报道的反应,即大家显示出对这个词如此强烈的抵制?你如何解释这种苛刻——米歇尔·福柯一谈精神性,立刻所有人都群情激奋,疑窦丛生。你会怎么解释这些?
FOUCAULT: 说这是无知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这不仅仅是无知的问题。为了解释我自己,我不得不在这里谈一些很私人的想法。 说实话,我反而对人们的诧异而感到诧异,因为我深受布朗肖和巴塔耶思想的影响。他们才是我的真正老师。于我而言,我与我青年时期的思想决裂的主要原因就是我读了萨特关于巴塔耶的文章。[18] 在萨特对巴塔耶的误读 (incomprehension) 中,似乎有某种东西向我解释了一种无法弥合的断裂,它指向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中无疑最根本性的某种东西。对哲学,对政治以及最终对我们所有人都至关重要的,是巴塔耶所谓的「经验」——它不是主体在其自身的持续进程中肯定自我。[19] 相反,它存在于某种断裂和随之而来的危险,在这之中,主体在与对象、他人、真理、死亡等等的关系中接受自身的嬗变、转化和消亡。这就是经验。是一种不再成为自己的风险。 至于我,我所做的不过是描述这种经验。疯狂史是什么?不就是通过这种经验,西方冒着风险构建其自身地位——即理性作为与疯狂相对的主体,最终将自身掌握为了知识的对象——的历史吗?[20] 所以我所做的也仅仅是这些。说到底,西方科学究竟是什么?难道不就是一种经验,构建出一个纯粹、固定的理性主体,来试图掌握或一种从头到尾都可以验证的话语,或一个可以从头到尾被实验的世界?这就是一种经验。真理不过是精神性的历史中的一个片段。
L'OBS: 现在,我希望你能帮助我思考一些实际上非常相似的事情,算是对你的观点的延伸。比如,当我们刚接触苏联的异见者时,知识分子们恰恰对他们反抗国家的态度中涉及精神性的方面表示出保留态度。索尔仁尼琴就是这种情况,他因为「我呼唤传统基督教」来反对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立场而受到许多原则性上的指责。当这些人来到西方时,他们的斗争得到了赞扬,但与此同时,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对他们言行中的精神性维度感到不安。

苏联作家,政治异见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8-2008) FOUCAULT: 精神性还是宗教性?
L'OBS: 根据你给予这些术语的含义,应该是两者兼有。
FOUCAULT: 他们肯定将精神性和宗教性混在了一起。我觉得,一个经历过1917年之后的俄罗斯人,无法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中找到精神性的原则,找到主体反抗意识 (soulèvement des sujets) 的信念。
L'OBS: 是这样的。
FOUCAULT: 所以应该由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回答,为什么在今天的苏联,主体的反抗意识只能依赖宗教来唤醒。
L'OBS: 当然。
FOUCAULT: 应该由他们来回应,而不是其他人。
L'OBS: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只是在思考一个纯粹的社会学问题。我直觉觉得这件事情的调性会大概率发生改变。人们对索尔仁尼琴行为中的精神性或宗教性维度表示保留(顺便说一下,你的区分在这里同样有效)。但我总觉得,恰恰相反,当下在伊朗发生的事情使那些曾经表达保留态度的人——或许出于某些误解,他们反而是喜爱你的报道的人——在霍梅尼和这种回归倒退的实践中发现了各种优点。这种激起伊朗人反抗意识的精神性维度被赋予了崇高的正当性,而最终支撑这一切的,恰恰是一个本应受到怀疑的宗教性内核。
FOUCAULT: 别问我为什么我的同时代人会有这种想法;光是思考我自己要思考的事情就足够头大了,我还得要去想象他们和我想法不一样的原因! 不过这里确实存在着一种肤浅化评判 (superficial valorization) 的现象,只要是一个伊斯兰国家,我们就必须支持它。而在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人中,你如果说在犹太语境中发现了同样的精神性运动,他们首先会产生疑虑。 我们几乎没怎么谈论到,例如,在佛教信仰中是什么情况,等等。至于我,重申一下,我认为这种通过主体试图的反抗来揭示 (mise à nu) 精神性的方式与当代世界历史中的某些事物是有联系的。当然,我的想法是,我们曾经试图从科学角度来构想一种革命项目的巨大失败——一种既能建立理性组织的国家,又能确保个人福祉的革命——是这种寻求精神性的意志如今以一种赤裸的形式重新出现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什么这种运动唯一能披上的外衣是宗教的原因。
L'OBS: 让这一运动披上这样的外衣,难道不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吗?毕竟我们既没有建议,也没有教训可以提供。一整个人口在对抗压迫性的国家极权主义的过程中,诉诸宗教,并最终希望回归某种宗教形式的国家,无论促使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难道这不会同时带来权力的混乱,充满各种可能的、可以想象的恐怖吗?简而言之,重新审视政教分离——或许这一概念不完全适用于伊朗的情况——难道不是蕴含着更大的危险吗?
FOUCAULT: 我觉得我们既要具体,也要谨慎。
L'OBS: 现在的情况很简单。很明显有一个像沙王那样的独裁者,带着他的警察施行酷刑,监狱人满为患、惨无人道。但与此相对的是,我们看到大量的愿景涌现出来,组织起来,并寄托于什叶派信仰中。如果这些愿景的承载者缺乏(实现它们的)力量,那很可能会导向一种极其恐怖、甚至更加专制的原教旨主义。我已经可以预见到许多人会开始流下鳄鱼的眼泪!
FOUCAULT: 如果你不介意,让我们回到我写的那篇文章。我清楚地记得,我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所引用的伊朗人的表述中,有令人不安和危险的方面;奇怪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看到的是某些受西方启发的政府形式的危险与宗教政府固有的某些危险的混合。[21] 比如,当我们问到:「那些在你们的伊斯兰政府中的宗教少数群体怎么办?」,回应一方面是经典的、陈词滥调的回应,而我们知道它有多危险——这是十八世纪的回应。他们说:「制定法律的多数人将决定如何定义少数群体的地位。」我们知道这一结局是什么。另一方面,这些相同的人告诉我们,某些宗教团体,例如巴哈伊教 (Baháʼí),[22] 信奉的是一种完全错误和堕落的宗教,容忍绝不可能。因此,你可以看到,最终其实是西方的理性主义思考——这种雅各宾民主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危险。这样的危险聚集在一起,威胁着伊朗运动,当然,也威胁着许多其他地方的运动。 伊朗人对此完全清楚——并非所有人都清楚,但那些我有机会与之深入交谈的人们都心知肚明;他们清楚地知道,问题在于是否能从伊斯兰教中汲取某些能让他们避免这些危险东西,因为而此时此刻,伊斯兰教既是他们的传统,是他们国家认同的形式,是他们战斗的武器,也是他们反抗意识的信念。所以,我不觉得我们要不停地告诉他们,「但你们正在倒退到一个充满原教旨主义风险的伊斯兰教中,无论如何它都是一种一神教,因此是不宽容的」,等等——我不认为以这种理由激烈地斥责他们,指责他们狂热,能有任何结果。他们不是狂热分子,但确实,正如我所说的,从这一运动开始组织成一个宗教国家或一个国家宗教时开始,那就有着狂热主义的危险了。 问题在于,要弄清楚在当代——我在这里为伊朗人发言,但也为所有人发言——我们能用这一在伟大革命希望的废墟之下,以赤身裸体重新出现的精神性的意志做些什么,它在这里以伊斯兰教出现,在那里以某种形式的基督教出现。
L'OBS: 在选举波兰教皇的过程中呢?
FOUCAULT: 也许吧——或是在环境保护主义中等等。它有上千种形式:有时是荒谬的,常常是令人不安的,有时感人,有时天真,有时微妙,但总是非常强烈地 (insistante) 贯穿于当代世界。
L'OBS: 也包括那些异端邪教 (sectes)?
FOUCAULT: 我们对此能做些什么呢?与其以实际完全背离整个宏大精神性努力的意识形态之名谴责它们,我们不如看看如何在它的框架内努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塔耶二十年前所提出的关于对精神性的关注 (preoccupation),至今对我来说依然没有过时。无论如何,这就是我正在为之奋斗的东西。
L'OBS: 最后,我希望你能展开这个想法: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精神性?我们可以利用什么东西来抓住它、构想它、接受它?
FOUCAULT: 经历了两个世纪,一种精神性才在基督教内部诞生。这一精神性仍然是基督教的,但却完全是与教会所对立的另一种形式,它改变了一些(坦率地说,许多)西方的东西。今天,站在我们所处的这片废墟之上,我不认为十年或十五年就能真正看到它可能的样貌。共同生活弟兄会、再洗礼派、塔博尔派等等的时代将会再次到来,虽然不会以宗教形式出现——当然,宗教的形式将依然存在;这将是一场至少持续一个世纪的大型实验,甚至更久。 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
L'OBS: 我们必须等待。
FOUCAULT: 不,不是等待——而是行动,实践!反抗意识必须被实践,我说的是必须实践拒绝自我所处的主体地位,拒绝自我的身份,拒绝自我的固定性,拒绝自我的本质。这是拒绝世界的首要条件。
L'OBS: 这是我们应该从例如集体自杀这种奇特却又参差的现象中所期待的东西吗?
FOUCAULT: 原来你为我设下的陷阱在这里![23]
L'OBS: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你所描述的东西)似乎支持了我刚才所说的内容,或者似乎与之具有相同的性质。我不知道这种性质到底是什么,但它的确很特别。在这种成为不同的存在、反抗意识中,你难道没有看到某种相似性吗?这一相似性是什么?
FOUCAULT: 这么说或许会显得过于笼统,但我们所缺失的是这一观念:大约在十八世纪,略早于法国大革命,曾经存在一个历史的主体 (a subject of history)。 这个历史主体曾经是理性、人性、人 (man) 等等——也包括社会。我们如今知道不存在什么历史的主体。历史并不会携带某个主体,而主体也不会携带历史。我认为这就是目前显现出来的东西。这种不愿意被历史主体所裹挟的反抗意识——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时代最为独特的现象。
L'OBS: 很好。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采访可以在这里结束了。谢谢你。/
[1] 原标题:"Political Spirituality as the Will for Alterity: An Interview with the Nouvel Observateur",原文出处:https://www.journals.uchicago.edu/doi/abs/10.1086/711138
[2] 采访者指的是米歇尔·福柯 1978年在意大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的邀请下特派伊朗所撰写的八篇报道之一,而这是米歇尔-福柯当时唯一一次援引政治精神性的概念来描述伊朗;见 Michel Foucault, "À quoi rêvent les Iraniens?" Dits et écrits, ed. François Ewald, Daniel Defert, and Jacques Lagrange, 2 vols. (Paris, 2001), 2: 694. 有关福柯为《晚邮报》所撰写的伊朗报道,请参阅 Janet Afary 与 Kevin B. Anderson 合著的Foucault and the Iranian Revolution: Gender and
the Seductions of Islamism (Chicago, 2005) 附录部分。——译者在原脚注基础上有所补充。
[3] 这里所指的应该是1978年-1980年土耳其爆发的前所未有,由极端右翼领导的政治暴力事件,这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了1980年的土耳其政变。——译者注
[4] 凯末尔主义 (Kemalism) 是以土耳其国民运动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 (Mustafa Kemal Atatürk) 所命名的政治意识形态,为土耳其共和国的建国意识形态。其六大基本理念为:共和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国家主义和改革主义。——译者注
[5] Bazaari是对伊朗商人阶级的统称,即在集市(bazaars)上工作的人。
[6] 福柯这一段的回答在访谈原文中被划掉了。
[7] 这里似乎是福柯第一次把精神性这一概念完整地归结至古希腊。
[8] 这一段在访谈原文中被圈出来了。
[9] 福柯在这里所说的「一个特定知识模式」是古希腊Technē(技术、技艺或艺术)这个概念。福柯对这个概念的提出与详细阐述见《主体阐释学》,尤其是1982年二月十七日的第一课时。——译者注
[10] 福柯在这里将精神性描述为有别于宗教,但又与宗教密切相关,这体现了他对穆斯林教中精神性这一概念的了解所产生的影响。福柯在准备伊朗之行时阅读了亨利·科尔宾(Henry Corbin)的著作,他特别分析了伊斯兰密教传统(尤其是伊斯兰诺斯替主义、神秘主义、哲学和诗歌)所援引的精神性概念,分析了它对历史和政治之外的时间性的依赖(科尔宾称之为 「元历史」),以及它对宗教概念的诉求,这种宗教概念与穆斯林社会和政治生活中预设的神权、司法和法律形式是相对立的;见 Henry Corbin, Corps spirituel et terre celeste: De l'Iran mazdéen à l'Iran shî'ite (Paris, 1960),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islamique (Paris, 1964), 和 En Islamiranien: Aspects spirituels et philosophiques, 4 vols. (Paris, 1971-1972)。福柯肯定认同这种灵性概念中的反司法资源(anti-juridical),以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历史权力结构(包括沙赫政权);此外,这种灵性概念所预设的主观性与真理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别于当代西方模式,而且更接近福柯的本意。关于科尔宾对福柯的影响,见 Laura Cremonesi et al., "Foucault, the Iranian Uprising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a Collective Subjectivity", Foucault Studies 25 (Oct. 2018): 299-311;Julien Cavagnis, "Michel Foucault et le soulèvement iranien de 1978: Retour sur la notionde 'spiritualité politique,'" Cahiers philosophiques 130 (Fall 2012): 51-71; and Andrea Cavazzini, "Foucault in Persia: Prima e dopo il Reportage Iraniano," in Michel Foucault: L'Islame la rivoluzione iraniana (Milan, 2005), pp. 41–48。以上注解的提出我由衷感谢 Haun Saussy 和 Daniele Lorenzini。
[11] 福柯对历史上宗教运动更为详细的阐述,见福柯法兰西学院讲座《安全、领土与人口》1978年三月一日的讲座。另见福柯对再洗礼派与什叶派精神性在伊朗的政治作用之间相似性的评论:「什叶派与欧洲中世纪末期直至十七、十八世纪的某些宗教运动之间的联系甚至相似之处令我惊叹不已」 (Foucault, "Dialogue between Michel Foucault and Baqir Parham," trans.
Afary, in Afary and Anderson, Foucault and the Iranian Revolution, p. 186)。
[12] 「我读过几本关于伊斯兰教和什叶派的书,我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因为什叶派在政治觉醒、保持政治意识、挑拨和煽动政治意识方面的作用在历史上是不可否认的……总的来说,尽管由于什叶派与国家权力在那个时期的靠近使其宗教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但宗教仍然发挥了某种反对的作用」 (Foucault, "Dialogue between Michel Foucault and Baqir Parham," p. 186)。
[13] 这里似乎是福柯的口误,因为他所指的危机发生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而不是十六世纪。
[14] "Tous les établissements en France couronnent le malheur du peuple: pour le rendre
heureux il faut le renouveler; changer ses idées; changer ses loix; changer ses moeurs; changer
les hommes; changer les choses; changer les mots……Tout détruire; oui, tout détruire;
puisque tout est à recréer" (quoted in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ed. L. G. Mitchell [New York, 2009], p. 168)。
[15] 此处与下文我将autre/alterity统一译为「异质性」而不是「他者性」,这主要出于一下两个考量。第一,福柯早期《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所常引援的他者性概念是根是植于存在主义对这一概念的阐述的,而(正如下文福柯自己坦白)福柯后来对自己早期思想的决裂,也是对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态度的决裂。在此,「异质性」这一翻译所想要强调的,是福柯此处对这autre一概念的引援恰恰不该以 「他者」所理解。福柯与自己早期思想和人道主义的决裂,见Behrent, Micheal C. 2013. "Foucault and Technology". 第二,我认为福柯晚期对于自我技术和精神性的强调与中期其对权力关系下的反抗是一致的,即在于自我对于自身主体位置细微且独特的「移置」,「转化」和「扰乱」所带来的根本断裂,而非单纯将自我创造为先验于主体的他者位置。而后者的理解恰好是「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缺乏批判性」这一误读的来源,尤见韩秉哲《精神政治学》。对于福柯后期对自我反抗与转化的伦理创造与萨特和存在主义的对比,见Engels, Kimberly. 2019. "Ethical Invention in Sartre and Foucault: Courage, Freedom, Transformation". Foucault Studies, no. 27 (December):96-116. https://doi.org/10.22439/fs.v27i27.5893. ——译者注
[16] 福柯在这里的阐述似乎与上文相矛盾,即法国大革命是唯一一个没有精神性的革命。
[17] 法文原文中采访者使用的一词是"désoccidentalisation"(去西方化)。但结合语境,采访者在此应该更有可能想说的是西方化 (Occidentalization) 这一词,我的翻译依此进行了变动。
[18] 见Jean-Paul Sartre, "A New Mystic: On Bataille’s Inner Experience," trans. Chris Turner,
in We Have Only This Life to Live: The Selected Essays of Jean-Paul Sartre, 1939–1975, ed. Ronald
Aronson and Adrian van den Hoven (New York, 2013), pp. 47–82.
[19] 对于福柯早期对乔治·巴塔耶的阐述,见Foucault, "A Preface to Transgression,"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trans. Donald F.
Bouchard and Sherry Simon, ed. Bouchard (Ithaca, N.Y., 1980), pp. 29–52. 对于福柯对自己与布朗肖和巴塔耶的关系的描述(发生在这次访谈的前几个月),见Foucault, "Entretien avec Michel Foucault," in Dits et écrits, 2:860–69.
[20] 见福柯《疯癫与文明》。
[21] 「人们常说,伊斯兰政府的定义并不精确。恰恰相反,在我看来,它们有一种熟悉的清晰度,但我必须说,并不太令人放心。『这些都是民主的基本公式,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还是革命民主。』我说,『从十八世纪以来,我们就没有停止过重复这些公式,你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Foucault, "What Are the Iranians Dreaming About?" trans. Karen de Bruin et al., in Afary and Anderson, Foucault and the Iranian Revolution, p. 206); 「有暴力反犹主义的示威,至少是口头上的。还有仇外示威......不仅针对美国人,还针对来伊朗工作的外国工人" (Foucault, "Iran: The Spirit of a World Without Spirit: Foucault's Conversation with Claire Brière and Pierre Blanchet," trans. Alan Sheridan, in Afary and Anderson, Foucault and the Iranian Revolution, p. 259).
[22] 在原稿中,巴哈伊 (Baháʼí) 以Mahi的形式出现,并伴有一个问号。看来福柯在这里指的很可能是巴哈伊教的信徒,该教在当地的容忍度仍存在很大争议。我感谢Behrooz Ghamari-Tabrizi提出这一点。
[23] 这里的背景是:1979年四月一日,福柯在法国同性恋杂志Le Gai Pied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赞扬通过自杀/死亡理解并体验快感的文章《最简单的快感》,这一文章当时被视为对极端暴力和自杀文化的肯定,发表后受到包括《世界报》在内诸多媒体和公众的猛烈抨击。同年四月十四日,他在《新观察家》上发表了一封致梅赫迪·巴扎尔甘 (Mehdi Bazargan) 的公开信,明确谴责伊朗政权的极端政治暴力,并试图对伊朗总理巴扎尔甘施加影响。《最简单的快感》一文,见https://www.generation-online.org/p/fp_foucault13.htm ——译者注
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备战深国交网”除发布相关深国交原创文章内容外,致力于分享国际生优秀学习干货文章。如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原谅,并联系微信547840900(备战深国交)进行处理。另外,备考深国交,了解深国交及计划参与深国交项目合作均可添加QQ/微信:547840900(加好友时请标明身份否则极有可能加不上),转载请保留出处和链接!
非常欢迎品牌的推广以及战略合作,请将您的合作方案发邮件至v@scieok.cn本文链接:http://www.scieok.cn/post/4808.html
-
<< 上一篇 下一篇 >>
我们时代的政治精神性:福柯与《新观察家》的访谈 / 翻译
29418 人参与 2024年10月25日 17:42 分类 : 深国交哲学社 评论
search zhannei
深国交2024年英美本科录取小计
-

未标注”原创“的文章均转载自于网络上公开信息,原创不易,转载请标明出处
深国交备考 |
如何备考深国交 |
深国交考试 |
深国交培训机构 |
备战深国交 |
联系方式
Copyright www.ScieOk.cn Some Rights Reserved.网站备案号:京ICP备19023092号-1商务合作
友情链接:X-Rights.org |中国校园反性骚扰组织 | 留学百词斩 | 南非好望角芦荟胶 | 云南教师招聘考试网 | 备战韦尔斯利网| 备战Welles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