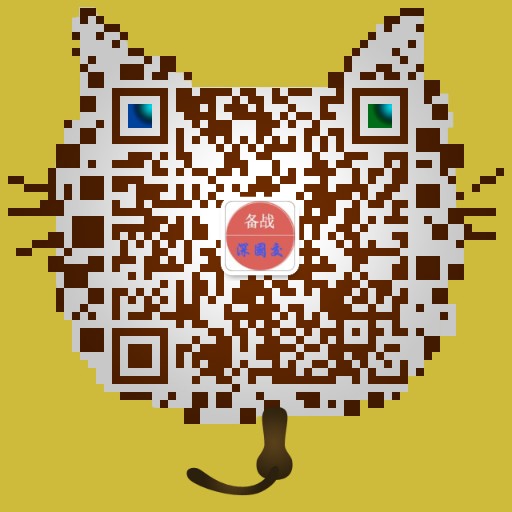当前位置:首页 » 深国交哲学社 » 正文
-
所谓证言不正义,就是发生于证言交换中的认知不正义。而认知不正义则是这样一种不正义,在其中,受害者作为知识拥有者的能力遭到错待 (be wronged) (Fricker, 2007, p. 20)。而在证言交换领域,说某人遭到这种错待,大体上就意味着,此人被不恰当地视为纯粹的信息来源 (source of information),而非同时被视为信息提供者 (informant)。我们能够从信息来源身上提取信息。例如,从一个人乱糟糟的头发上我们就能推测出外面风很大。与之相对,信息提供者则能够主动提供信息,而非仅仅是被动被提取信息。例如,我信任的水管工告诉我往马桶里丢太多的纸会堵塞下水道,他通过言语行为向我主动传递信息,他对于我而言就是一个信息提供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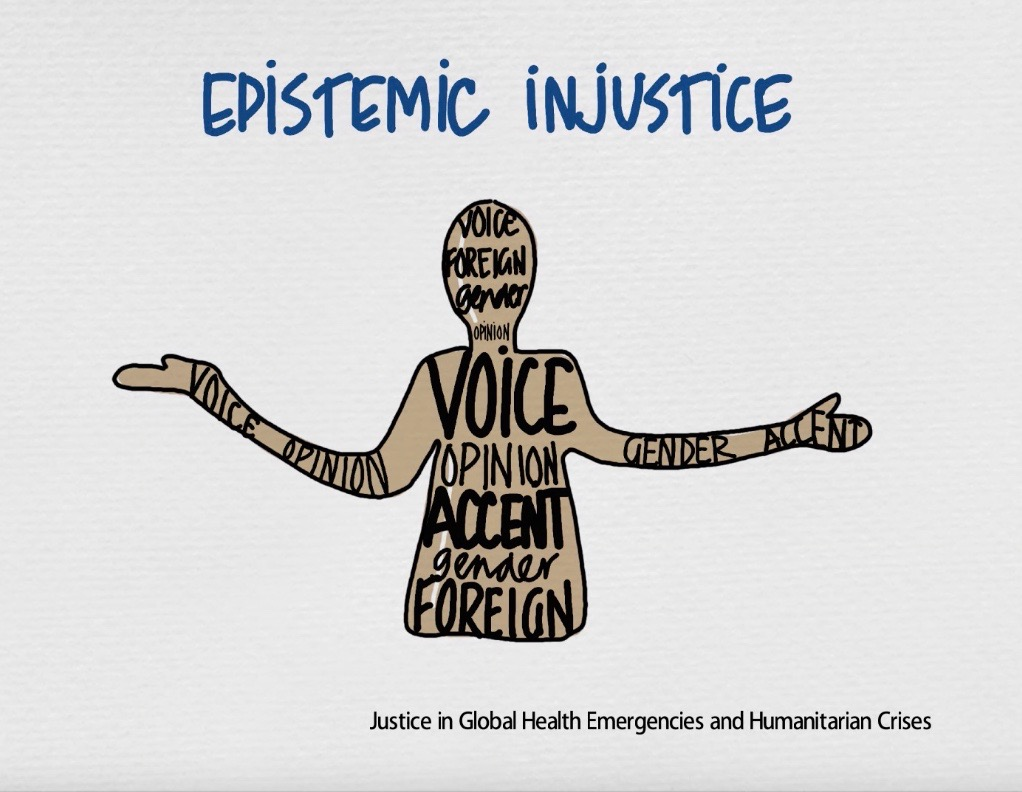
将某人视为纯粹的信息来源,是对其进行认知物化 (objectification)。也就是说,此人从一个能够主动传递知识以帮助他人的认知主体,被降格为纯粹的认知对象 (Fricker, 2007, pp. 132-133)。对于认知主体和对象的区分,建基于我们的某种规范性期待 (normative expectation),这种规范性期待则衍生自我们进行认知协作的需要。我们有指望他人来收集信息的需要,这使我们期待说话者抱有传递准确信息以促进认知协作的目的。若我们将某人视为信息提供者,我们就对其持有这样的规范性期待。但是若说话者仅仅被视为信息来源,那么我们就对其没有这样的期待(Craig, 1990, p.36)。因此,认知物化意味着将说话者排斥在进行认知协作的认知共同体之外。 这与某些对于信任 (trust) 的解释非常接近。根据这些解释,如果我们信任某人,我们就对她有一种规范性期待 (Hawley, 2014)。而对于那些我们没有这种规范性期待的人而言,我们最多只能依赖 (rely on) 他们。因此,正是规范性期待的存在与否划定了信任和依赖之间的区别。信息提供者和信息来源之间的区别也是如此。 简言之,认知不正义中包含的错待是一种不恰当的认知物化。也就是说,这种错待的内容是认知物化,而这种认知物化采取了不恰当的形式。(有些哲学家认为,在物化之外,认知不正义带来的错待还包括听者未能给予说话者应得的认可 (recognition) (Congdon, 2017, pp. 248-250)。这一观点本身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在本文中我将不讨论这一观点。这是因为,仿照下文的论证,我们也可以认为,若认可的缺失要成为错待的一部分,它本身也得是不恰当的。因此,如果读者认为认可的缺失确实是认知不正义的一部分,那么他们可以直接将上述「不恰当的物化」替换为「不恰当的物化或者认可的缺失」。这对本文的论证没有实质性影响。)在此,「不恰当」这一限定是很重要的。这是因为,并非每一物化都能够构成错待。以下这组例子佐证了这一点: 种族歧视的陪审团
Tom是一个生活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的年轻黑人。他被指控侵犯了一个白人女孩。即便有很强的证据表明Tom是无辜的,法庭上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出于根深蒂固的种族仇恨仍然坚持认为他犯下强奸罪。结果,Tom不出所料地被投入监狱。  《杀死一只知更鸟》中Tom的原型
《杀死一只知更鸟》中Tom的原型臭名昭著的骗子
有个骗子在街坊很出名,因为他经常欺骗他的邻居。有天他的房子着火了。于是他高声呼救,希望有人来帮他灭火。但是考虑到他斑斑的劣迹,没有人前来救助,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不过是另一个骗人的把戏罢了。所以直到有人亲眼看见了他的房子烧起来了,人们才跑过去救他。 在第一个例子中,Tom被物化了,而且其作为知识拥有者的能力似乎确实遭到了错待。事实上,他以及几乎所有同时代黑人都经常遭到类似的错待。然而,尽管骗子的街坊也不把骗子当成一个信息提供者,他似乎并没有受任何错待。类似地,因为劣迹而被学术界拒之门外的科学家也似乎没有遭到错待,尽管他们也不被当作是信息提供者。这种遭遇完全是他们应得的。 所以,究竟是什么使一些认知物化构成一种错待,而另一些则不构成错待?是什么构成这种错待独有的不恰当性?例如,是什么将种族歧视的陪审团和臭名昭著的骗子区分开来?Miranda Fricker的回答是,如果听者因为其偏见而低估了说话者的可信度,那么说话者就遭到了错待,也就是说,她就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被物化了。在种族歧视的陪审团中,Tom是种族主义偏见的受害者,因此他受到的不信任构成一种对其知识拥有者能力的错待。然而,在臭名昭著的骗子中,街坊对骗子之不可信的判断并不是出于偏见,而是基于某些对于他过往行为的合理归纳。总之,根据Fricker的解释,正是偏见使得某些认知物化构成一种错待。 我们暂且同意,偏见就是使认知物化构成错待的关键特征。但是仍然有一个进一步的问题:为什么是这样?凭什么偏见就能使认知物化构成一种错待?换句话说,究竟是偏见的什么特征使得其导致的可信度不足(例如,种族歧视陪审团)能够不恰当地物化说话者,从而构成一种错待;而其他的可信度不足则不能(例如,臭名昭著的骗子)?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讨论这个问题。在第一节,我将介绍Fricker基于听者的道德可谴责性 (moral culpability) 的解答,以及她为了回应一些反例而对该解答做出的修正——一种基于道德责任 (moral responsibility) 的解答。在第二节,我将批评这一修正后的解释。我将论证,它与其一开始的动机背道而驰,并且会低估一些证言不正义对说话者的错待。在下一节,我将审视恰当的释然情绪 (relief) ——我们的释然表明我们认为某种错待并不存在;而这种释然是恰当的,仅当我们所认为的错待确实不存在。我继续论证,Fricker修正后的解释仍不能说明为何我们的某些释然是恰当的。这表明听者的道德责任最多也只能是奠定错待的诸多因素的一种;为了说明认知不正义中的错待,我们可能需要一种多元的解释,需要援引除了道德责任之外的一些其他因素。在结尾部分,我将试探性地提出其中一种值得研究的因素。  Fricker基于道德责任的解释
Fricker基于道德责任的解释Fricker对于上述问题——即「究竟是偏见的什么特征使得其导致的可信度不足能够不恰当地物化说话者,从而构成一种错待」——的最初回答是:如果听者受到偏见影响,那么她就是道德上可以谴责的;而正是这种道德上的可谴责性解释了为什么偏见带来的可信度不足构成对于说话者的错待。用她的话来说, ……伦理上无可谴责的错误并不能破坏或者以其他方式错待说话者。似乎证言不正义中含有的伦理之毒必须衍生自听者的判断中含有的伦理之毒。而如果听者的错误是伦理上无可谴责的,那么这种伦理之毒便不存在 (Fricker, 2007, p. 22)。
有利于她的解释的一个理由是,关于说话者可信度的任何无辜的错误似乎都不能构成对于说话者的错待。如下例子就属于这一类: 羞涩的Smith
Smith实在是太胆小了,以至于每次他和别人说话,他都避免接触对方的目光。有一次,和他说话的人注意到这一点,并且想起一条可靠的原则,即,那些说话时不敢看你眼睛的人很有可能是骗子。于是,这位听者得出结论:Smith并不可信,完全是在编造谎言。 在这个情形中,Fricker会认为听者是无可谴责的,因为我们并不能合理期待一个普通人能够意识到Smith的行为并不是其不诚实的表现,而只是体现了羞涩的性格。要发现这一事实,我们就得拥有强大的读心技能。听者在此犯下的错误更大程度上来自坏运气——她只是恰好将一条事实上可靠的原则运用于它的例外上了。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这种可靠原则的例外情况也算是一种证言不正义,那么证言不正义的发生就过于容易了,甚至臭名昭著的骗子也会被算作是证言不正义的例子,因为它确实也是街坊们可靠归纳的一个例外。Fricker基于道德可谴责性的解释就能够避免这一不恰当结论。臭名昭著的骗子和羞涩的Smith的共同点在于,就其关于说话者的可信度判断而言,听者都不是道德上可谴责的,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些案例中不存在任何证言不正义 (2007, pp.42-43)。到现在为止,Fricker的解答能够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然而,Fricker很快就意识到,真的存在一些无可谴责的证言不正义: 不幸的Herbert
Herbert生活在上世纪50年代,他和他同时代人缺乏对于发现性别偏见而言至关重要的批判性资源。这使得他甚至不能处于发现并纠正性别偏见的恰当位置上。结果,在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上,Herbert因为性别偏见而无端压下了Marge的意见,而不管Marge确实向他呈现了一些强有力的证据。 可以论证,Herbert在此犯下的错误是无可谴责的。这里的基本逻辑是,如果某人不能意识到一件事情的消极道德地位,那么她就不应当为做了这件事而受到道德谴责。人们广泛承认,道德可谴责性依赖于某些认知条件的满足。这就是说,如果主体本身就对一些事情一无所知,而这种无知又是无可谴责的,那么她就不应当受到道德谴责 (Le Morvan & Peels, 2016)。这些认知条件之一就是,主体必须对自己行为的道德意义 (moral significance) 有着某些意识。根据这个观点的一个版本,这里所要求的意识是一种从言 (de dicto) 意识:主体必须将其行为看作是道德上坏的 (Zimmerman, 2002)。另一种弱一些的版本则只要求某种从物 (de re) 意识,即主体必须意识到其行为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事实上具有道德意义(Harman, 2011)。 在不幸的Herbert中,Herbert的行为具有的道德上有意义的特征就是影响其可信度判断的偏见。然而,在缺少批判性资源的情况下,关于这种偏见的道德意义,他既不能获得从言意识,也不能获得从物意识。既然没有相应的批判性资源,他就不能设想这种性别偏见的存在,遑论将其与其带来的行为设想为道德上坏的。此外,他的这些意识的缺乏本身并不是可以指责的。这种缺乏属于当时历史背景中的空白,而非他自己的理智失败。因此,我们可以认为,Herbert确实是道德上无可指责的。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会认为,Marge以及几乎所有同时代女性都遭受着认知不正义,也就是说,她们受到不恰当的认知物化。考虑到Herbert在道德上的无可谴责,不幸的Herbert确实构成Fricker基于可谴责性的解释的反例。 Fricker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作为回应,她论证说尽管我们不能合理地谴责Herbert,我们仍然可以对他感到某种程度的失望 (disappointed)。这种失望是一种具有道德负载的 (morally loaded) 反应态度 (reactive attitude),其意味着我们认为他是道德上负有责任的 (morally responsible),尽管其程度可能要比道德可谴责性来得弱一些(2007, pp. 103-104)。Fricker论证说,这种失望的根据在于对于其可用的批判性资源的常规 (routine) 使用和例外 (exceptional) 使用之间的区分。他的偏见性可信度判断反映了当时对于女性的一种常规态度。然而,考虑到他当时所能获得的批判性资源,他原则上仍然能够将这些资源以一种进步的、新奇的方式进行组合,以抵消性别偏见的作用,尽管其并不具备性别偏见的观念 (2007, pp. 104-105)。例如,他在原则上仍然可能将更多的关注放在Marge提出的那些证据本身,或者更加仔细地考虑Marge在相似事情上的证言的过往履历是否可靠。总之,与仅仅遵循当时的通行操作相比,他的行为确实还有改善的空间。既然如此,即便Herbert并非道德上可以谴责,我们也仍然能够对其感到失望,因为他没有做出什么抵抗就屈服了当时性别意识形态的淫威。因此,Herbert仍然在道德上负有责任。这种道德责任就解释了为什么Marge在此情形下仍然受到了错待。 根据这个回应,Fricker的解释应当做出如下修改:如果听者受到偏见影响,那么她就在道德上负有责任;而正是这种道德责任解释了为什么偏见带来的可信度不足构成对于说话者的错待。这个修改后的解释能够容纳Marge确实受到错待的直觉。  对Fricker修正后解释的批评
对Fricker修正后解释的批评Fricker的回应极富洞见。但是,这个回应以及修改后的解释是否能够实现Fricker原本的目的?这并不明显。我的第一个担忧是,这个修改后的解释似乎意味着,在羞涩的Smith中,也存在构成证言不正义的那种错待。首先要明确的是,如果我们降低听者的道德责任的标准,即认为听者无须值得谴责而只需负有一定的道德责任就能够错待说话者,那么,仅仅指出听者是无可谴责的便不足以表明其并未错待说话者。此外,人们可能论证说,在羞涩的Smith中,尽管我们并不能合理期待一个普通人能够充分察觉到Smith的羞涩性格,但听者无论如何也可以做得更好。或许,她事先就可以提高自己对于可靠原则的例外情况的敏感性,这样她就能够对类似的羞涩更加敏锐。因此,一旦Fricker对其解释做出上述修改,我们便不能保证,将一个可靠原则用于其例外之上并不构成证言不正义。但是正如上一节已经指出的,区分这类例子与真正的证言不正义,正是Fricker的解释的一大重要动机。 类似地,根据修改后的解释,Elizabeth Anderson (2012) 举出的结构性证言不正义的例子其实也很可能并不是真正结构性的。结构性证言不正义的基础并不在于双方的个别交换当中(例如,一方欺骗或者强迫另一方),而在于作为这些交换的背景的社会结构。例如,由于某种群体内偏袒 (in-group favoritism),从属于特权群体的听者可能会认为,从属于非特权群体的说话者不如同属于特权群体的伙伴来得可信。由此导致的不信任是典型的结构性不正义,因为群体内偏袒是一种道德上无辜的心理倾向;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倾向将业已存在的结构性不正义投射到认知协作的领域。然而,即便在这个例子中,听者似乎也对其可信度判断在道德上负有责任,因为我们会对她感到某种程度的失望。毕竟,她的判断仍然有改善的空间。或许,她作为特权群体的成员,尤其应当对群体内偏袒和现有的社会不正义之剑的共谋更加敏感。这样一来,根据Fricker修改后的解释,在这个证言交换内,说话者仍然遭到了听者的错待。因此,这个所谓的结构性不正义的例子其实是虚假的:我们毕竟能够在此个别交换中找到不正义的基础——听者的道德责任。这里的关键和上面关于羞涩的Smith的讨论类似:一旦我们我们降低听者的道德责任的标准,那么我们便不能够保证存在真正的结构性证言不正义案例。这是因为,在任一所谓的结构性案例中,尽管听者确实无可谴责,我们或许仍能够找到听者的道德责任。 另一个担忧则源自这样一些例子,在其中听者比Herbert做得要好得多,但是仍然由于坏运气而难逃偏见的影响。 早期反种族主义者
Caren是一个生活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女性。她萌生出反种族主义的想法已经有些年头了。尽管她生长在充斥着种族歧视偏见的环境中,但是基于她的个人经验,她仍然成功意识到,有色人种比主流意识形态所认为的要可信得多。自此以后,出于自己的良心,她付出了很多努力去对抗种族歧视偏见对自己可信度判断的影响(尽管她尚未形成种族歧视偏见的概念)。例如,在与有色人种交谈时,Caren会尽其所能地质问自己:要是对方是一个白人,我又会怎么做?尽管当时并没有任何批判性资源可以用来反思种族歧视偏见,但是这种策略仍然在事实上是有效的。然而,这种策略需要Caren进行许多有意识的努力,因此,当她没有足够精力时,她即便尽其所能也很可能最终会受到偏见的影响。 尽管Caren和Herbert的可信度判断都受到偏见的影响,但是我们对于Caren的失望程度会低得多。毕竟,她确实创造出了一种使用当时可获得的批判性资源的进步性方法。她也尽其所能将其运用于许多情形中。只不过,她没能将其运用于上述的个别情形中。人们甚至可能进一步论证说,她并不对这个个别的失败负有道德责任,因为这个失败完全源自某种坏的环境性运气 (circumstantial bad luck)。如果这个解读成立,那么早期反种族主义者便不仅是真正的无可谴责的认知不正义案例,更是一个真正的不存在道德责任的认知不正义案例。然而,为了论证之便,我们暂且假设Caren确实对其可信度判断受到偏见的不当影响负有最小程度的道德责任。 但是,让我们回忆一下第一节引用过的Fricker的话:「证言不正义中含有的伦理之毒必须衍生自听者的判断中含有的伦理之毒」(2007, p.22)。对这句话有一个非常自然的解读,即,听者在道德上负有更大的责任意味着说话者受到更深的错待。这意味着,早期反种族主义者中的有色人种受到的错待是极为微小的,因为Caren仅仅在最小程度上负有道德责任。但是这么一种微小的错待究竟能够称得上是一种不正义吗?我认为,不正义是一个道德上更「厚实」的观念。因此,Fricker修改后的解释可能会使说话者受到的错待不能构成一种不正义。实际上,对于羞涩的Smith也可以做出相似的结论。我已经论证了,Fricker修改后的解释意味着这个案例属于认知不正义。但是同样地,即便我们同意Smith确实如Fricker修改后的解释所认为的那样遭到了错待,我们仍然可能不愿意将这种微小的错待视为一种不正义。 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是:种族歧视的陪审团和早期反种族主义者中包含的错待究竟有何区别?Fricker修改后的解释似乎会认为,后者与前者相比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是因为,种族歧视的陪审团在道德上简直不可饶恕,而Caren则只在最小程度上对其可信度判断负有道德责任。我认为这一看法并不合理。两个案例中的说话者似乎都受到了某种可观的错待;与此同时,在种族主义陪审团中,陪审团的可谴责的种族主义态度又给它额外添加了一层。这一点可以通过考虑我们对这两个案例的的反应态度来得到体现。在读到早期反种族主义者时,我们可能会对Caren有些许的失望。但是在此之外,我们还会对当时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氛围感到极度的失望甚至义愤,这种氛围阻挠Caren形成健全的可信度判断,一旦Caren放送警惕,它就会趁虚而入。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反应态度。标准的反应态度(例如感激、骄傲或者义愤)都是针对单个个体的,我们通过这种反应态度而谴责或者表扬某些个体 (Strawson, 1974)。但是当我们对某种意识形态感到义愤,我们并不是在将道德责任赋予任何一个个体,而是赋予某种非主体的东西 (non-agential)。作为对比,在了解到种族歧视陪审团后,我们会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形成相似的态度。此外,我们还会对陪审团这个个体产生强烈的义愤,因为他们在强有力的证据面前本来能纠正偏见产生的影响。我们期待他们拥有对低限度的良心,但是他们连这个期待都没有实现!如果我们认为,这些消极的反应态度能够指示说话者受到的错待,我们就能够得出结论说,尽管Tom确实受到更深的错待,但是在两个案例中,说话者至少都受到了某种程度可观的错待。  释然与错待
释然与错待除开这些担忧,Fricker修正后的解释似乎也不能很好地解释我们的某些释然情绪。当我们起初认为我们受到错待,但是后来获知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会感到释然。例如,假设我们羞涩的Smith觉得自己因为听者的不信任而受到了错待。但是,听者后来从别人那里听说Smith的行为不过是他羞涩的表现,而非不诚实的标志。于是,她找到Smith,为自己的误解向他道歉。对于Smith而言,感到释然是非常自然的情绪。他对自己说道:「这不过是一次偶然的误解而已。不好的事儿确实是发生了,但至少她对我并无恶意,我没理由去谴责她。」他感到释然,这是基于他认为他并没有遭到错待。 我们可以合理认为,我们的释然是恰当的,仅当我们所认为的错待之不存在是真实的。也就是说,Smith后来的判断是准确的,他确实没有遭到听者的错待。如果这个被认为不存在的错待实际上确实存在,那么释然就只能是一种自我安慰 (self-consolation)。换句话说,释然作为一种态度,其试图捕捉的标靶 (target) 是错待的不存在,而它的成功条件 (success condition) 正是错待之真实的不存在。 然而,除了这种听者确实无可谴责的情形之外,恰当的释然还可能存在于其他情形中。例如: 小众的阴谋论组织
Jack是一个本地瑜伽俱乐部的教练。在Jack所在的城市里,有一个小众的阴谋论组织。这个组织的核心信条是,所有左撇子都是完全不可信的,因为他们都是火星人派来地球的间谍。除了这些人以外,没有其他人相信这个说法。有天,Jack在他的瑜伽课上遇见了好几个该阴谋论组织的成员。他们发现,Jack经常使用他的左手。于是他们认为,Jack是不可信的。不出所料,当Jack试图教他们正确的瑜伽动作时,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拒绝了他的教导。Jack为此感到困惑和沮丧。后来,他知晓这些人都是上述这个小众阴谋论组织的成员,全都对左撇子怀有很深的恶意。了解到这一点,尽管Jack仍然感到不爽,但他也在某种程度上释然了。「这只是他们的问题」,他想。 在这个案例中,Jack是证言不正义的受害者。Fricker基于道德责任的解释会说,Jack受到了错待,是因为听者对于他的偏见性判断是值得谴责的。单就后者这一点来说,这确实是正确的。但是这似乎并不是故事的全部。问题在于,Fricker的解释究竟该怎样容纳Jack释然之恰当。他的释然是基于他认为他可能受到的错待实际上并不存在;而这个释然情绪若是恰当的,仅当他确实没有被如此错待。但是根据Fricker的解释,听者的道德责任(包括道德可谴责性)就是说话者在证言不正义中可能遭受的错待的唯一基础。换言之,所有相关的错待的存在或者不存在都得由听者是否是道德上负有责任的来解释。因此,如果在此案例中,确实有某种错待不存在,那么听者必须在道德上不负有责任。因此,根据Fricker的解释,Jack的释然情绪若是恰当的,听者必须在事实上不负有责任。因为,只有听者道德责任的缺失才能造成错待的缺失。但是,考虑到阴谋论的听者确实是值得谴责的,Fricker的解释意味着Jack的释然不可能是恰当的。然而,我认为他的释然可以是恰当的——确实有某种错待缺失了。 我们似乎需要某种多元解释,以说明为何Jack的释然可能是恰当的。也就是说,我们或许可以找到其他不同于听者的道德责任的因素,作为偏见性可信度不足中的错待的基础。因此,偏见性可信度不足就可能以多种方式错待说话者,听者的道德责任仅仅是其中之一。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说,Jack的释然可能是恰当的,因为他只是遭到某些方式的错待,而没有受到其他的错待。具体来说,阴谋论的听者既然是道德上可谴责的,那么Jack释然的恰当性应是由某些其他构成错待的因素的缺乏而得到解释。 Fricker的同情者可能会回应说,Jack的释然的恰当性在Fricker的一元论解释框架下也可以得到说明。具体来说,他的释然不一定只能由某些错待的缺席而得到解释,而可能由所涉及的偏见种类而得到解释。这个回应依赖于Fricker对系统性 (systematic) 和偶然性 (incidental) 证言不正义的区分。系统性证言不正义包含的偏见(例如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偏见)可以「让人们易受到证言不正义以之外的诸多不同不正义的影响」(Fricker, 2007, p. 27)。与之相比,偶然性证言不正义则不包含这种类型的偏见,也就是说,偶然性证言不正义所包含的偏见不会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回应者可能借此论证说,Jack之所以感到释然,只是因为他发现他在这个情形中并非任何系统性证言不正义的受害者,而仅仅是某种偶然性证言不正义的受害者。因此,我们并不需要像上述多元解释那样,举出不同于道德责任以外的其他因素以奠定说话者可能受到错待的其他途径。 诚然,当我们认为我们遭受系统性证言不正义,但是后来获悉并非如此时,我们可能会感到释然,因为我们现在至少知道我们并不会在广阔范围内遭受不正义。然而,这一思路并不能运用到如下案例中。假定一个权威期刊的编辑出于偏见认为我不可信(可能她不负责任地鄙视我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并因此拒了我的稿,但是后来我在与期刊委员会的交流中获悉,这并不能代表期刊委员会的态度。知晓这个事实以后,我可能恰当地感到某种程度的释然。在这个例子中,我的释然基于我认为我并没有由于偏见而被期刊委员会拒绝。这是偶然性证言不正义的典型案例,因为关于研究方法的偏见,甚至几乎所有学术界特有的偏见,都不会使我易受其他种类社会不正义的影响。因此,即便在我认为我没有受到某种偶然性证言不正义,但后来得知并非如此的情况下,我仍然可以恰当地感到释然。因此,确实存在一些例子,在其中我们的恰当的释然并不能由系统性和偶然性证言不正义的区别来解释。但是,某种多元解释则可能说明我在此案例中的恰当释然:我的释然是恰当的,因为尽管我确实被值得谴责的编辑错待了,我仍然可能没有在其他方面被错待。  余论
余论在本文中我已经论证,Fricker修正后的解释并不是如同其原始版本一样具有良好的动机,且其可能低估了某些证言不正义所包含的错待。另一个担忧则是,它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的某些释然是恰当的。为了解释这一点,我们可以诉诸一种多元的解释,这种解释认为,一些不同于听者的道德责任的其他因素也可能奠定偏见性可信度不足包含的错待。 对于这些「其他」因素,一种可能的选项是边缘化 (marginalization)。根据Iris Young (1990),边缘化是一种结构性压迫,它「剥夺了以一种得到社会界定和认可的方式施展能力的机会」(p. 54)。所谓结构性压迫,就是说这种压迫并不能被恰当地归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压迫者或者压迫群体,而是某些通行操作,例如社会的风尚、习惯,或者制度性机制的结果 (Young, 1990, p. 41)。意识形态中所含有的偏见恰可构成这种意义上的边缘化的一种形式。例如,当代意识形态中性别或者种族歧视的偏见,剥夺了某些社会群体以得到社会承认的方式做出认知贡献的机会。因此,这种偏见带有某种结构性的压迫力量:说话者是在意识形态氛围中被边缘化、被压迫,而非被某些特定的人压迫。在这方面,做出偏见性可信度判断的听者更像是意识形态边缘化的提线木偶,是这种意识形态表达自身的工具,尽管这并不否认她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对其偏见负有道德责任。若我们认为受到压迫,尤其是受到结构性压迫就意味着受到错待,那么意识形态中的偏见造成的边缘化确实构成另一种错待的基础。根据这一思路,受到偏见性可信度不足影响的说话者至少可以同时遭受两种错待:首先,他们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边缘化;其次,他们还可能遭到道德上负有责任的听者的错待。这似乎能够解释为什么Jack的释然可能是恰当的,也能解释为什么早期反种族主义者中的错待仍然具有可观的程度,以及我们的反应态度所包含的那种不指向特殊个体的义愤。/ 参考文献
Anderson, Elizabeth (2012). Epistemic Justice as a Virtue of Social Institutions. Social Epistemology 26 (2):163-173. Congdon, Matthew (2017). What’s wrong with epistemic injustice? Harm, vice, objectification, misrecognition. In Kidd, Ian James & Medina, José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pistemic Injustice. New York: Routledge. Craig, Edward (1990). Knowledge and the state of nature: an essay in conceptual synthe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ricker, Miranda (2007). 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man, Elizabeth (2011). Does moral ignorance exculpate? Ratio 24 (4):443-468. Hawley, Katherine (2014). Trust, Distrust and Commitment. Noûs 48 (1):1-20. Le Morvan, Pierre & Peels, Rik (2016). The Nature of Ignorance: Two Views. In Peels, Rik & Blaauw, Martijn (eds.), The Epistemic Dimensions of Ignor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rawson, Peter Frederick (1974). Freedom and Resentment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Young, Iris Marion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Zimmerman, Michael J. (2002). Controlling ignorance: A bitter truth. 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 33 (3):483–490.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Philosophia 哲学社
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备战深国交网”除发布相关深国交原创文章内容外,致力于分享国际生优秀学习干货文章。如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原谅,并联系微信547840900(备战深国交)进行处理。另外,备考深国交,了解深国交及计划参与深国交项目合作均可添加QQ/微信:547840900(加好友时请标明身份否则极有可能加不上),转载请保留出处和链接!
非常欢迎品牌的推广以及战略合作,请将您的合作方案发邮件至v@scieok.cn本文链接:http://www.scieok.cn/post/4503.html
-
- 道德责任与决定论 -- 直觉认为可自由进行选择和行动,是真的吗
- 弱者的勇气:无权者的权力
- 什么是性许可(Sexual Consent)?复杂情况的分析和应用(上)
- 游戏世界里的第二性:社会性别作为本土电子游戏的重要分析范畴
偏见导致的不信任为何构成一种错待?
39260 人参与 2024年01月02日 15:59 分类 : 深国交哲学社 评论
search zhannei
深国交2024年英美本科录取小计
-

未标注”原创“的文章均转载自于网络上公开信息,原创不易,转载请标明出处
深国交备考 |
如何备考深国交 |
深国交考试 |
深国交培训机构 |
备战深国交 |
联系方式
Copyright www.ScieOk.cn Some Rights Reserved.网站备案号:京ICP备19023092号-1商务合作
友情链接:X-Rights.org |中国校园反性骚扰组织 | 留学百词斩 | 南非好望角芦荟胶 | 云南教师招聘考试网 | 备战韦尔斯利网| 备战Welles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