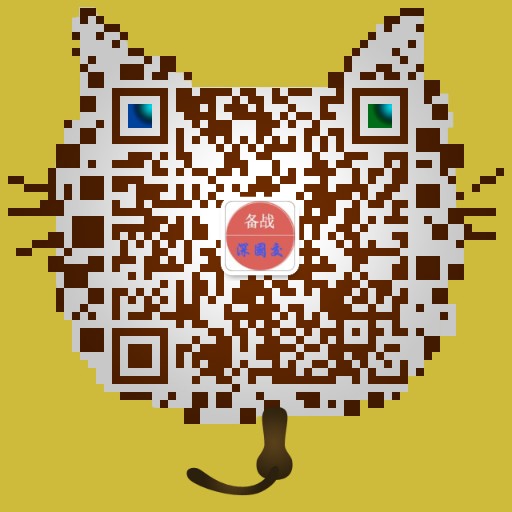当前位置:首页 » 深国交哲学社 » 正文
-
因为一个有教养的人的特点,就是在每种事物中只寻求那种题材的本性所容有的确切性。——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
「西方思想憎恶真空。对真空的开敞不过是眩晕。虚无被巴门尼德所放逐,它在智术中取得了胜利,后来又在神秘主义与虚己 (Kenosis) 的神学中凯旋。但和虚无的这种关系激起了怀疑;而被认定为智者常常是抱着轻蔑的。它污蔑一种思想,这种思想被指责为和无物有关,只有和它自身的关系,而它本身是空虚的。」2 马尔蒂尼的这一——完全准确的——陈述立即引发了一个问题。思想和这里的三个同义词——虚无、真空、开敞——所意指的东西能够拥有一种不同的关系吗?它能够避免——不管是否是出于疏忽——将巴门尼德对非存在的封锁永久化,避免将它贬斥为无效和虚空吗?的确,确证了这一封锁的主要是关于非矛盾律的逻辑需求。关于「非存在」,如果不预设这个指定了它的词,即虚无,命名了某物,也就是说,如果不断定它是存在的,就不可能对于它说出任何事情——而这是自相矛盾的。因此,这个疑问甚至在被提出之前就已被决定了:我们对于虚无所能说的一切,就是它不存在,这也就等同于将虚无排除出了逻各斯的宇宙。对于虚无,除了它是虚无以外,人们只能什么都不说 (say nothing) ,关于它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思想将虚无从可思的东西中划去,这一举动也被悖论性地再次承认下来。因为坚持说虚无什么也不是,不外乎就等同于在其本质中界定了虚无。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以根本不愿知道无来知道无。」3当然,通过这一悖论,对于无、无的地位,或者对于思考无的必然性,我们还没有说上什么。但是,至少有一个界域被标定出来,作为疑问本身在其中被提出的界域,而这一界域就是思想与逻辑之间的关系的疑问之界域。正如海德格尔所强调的那样,问题在于,为了评估思想,「逻辑」是否「是最高的法庭」4,抑或相反,「『逻辑』之观念本身」是否会「消解于一种更为源始的追问的漩涡中」。5

《雅典学院》中的巴门尼德丨Wikipedia
但这一漩涡从何而来?海德格尔会这样回应:从存在本身的追问中来。按照他的观点,存在与虚无是「相同的」 (dasselbe) ,它们共同的锁闭遮蔽了西方思想之作为存在神学的统一性。但是,使逻辑屈服于一个更高的权威,这一事实本身难道不是已经使我们陷入了完完全全的非理性主义吗?这的确就是「形而上学是什么」这篇讲座通常被理解和评判的方式。在二十世纪的整个哲学传统那里,情形都首先就是如此,它们在命题分析中仅仅看到了严格的方法,而在逻辑本身中看到「哲学的本质」6。但是在哲学中,逻辑难道不是应该扮演平凡的工具角色,作为探寻真理的工具吗,正如亚里士多德赋予它的角色一样?那么,没有什么会阻碍我们反过来追问逻辑,追问它的前提、可能性与限度。如果我们来仔细地考察的话,这就是海德格尔的主张。但这个主张值得被辩护吗?为了尝试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回到20世纪30年代初,回到卡尔纳普与海德格尔之间的历史性辩论。随后,我将尝试拓宽问题,并就虚无这一主题阐述这一疑问,即现象学是否(并且在何种条件下) 能够对虚无说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而不会放弃将现象学奠基为如是——现象-逻辑 (phenomena-logy) ——的东西:对逻各斯的需求 (requirements of logos) 。

争辩的起始点:「形而上学」的两种形象
在进入卡尔纳普与海德格尔的争论之前,回顾1929年讲座「形而上学是什么?」的主要内容并非多余,卡尔纳普发表于《认识》 (Erkenntnis) 第二期的文章,《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便回应了这次讲座。7
海德格尔讲座的全部原创性便在于其现象学风格。事实上,它涉及到的是一种方法,那就是根据形而上学本身如其所是地呈现形而上学,或者让形而上学基于其自身贯穿和渗透生存的方式来呈现自身,让形而上学在人类之生存的层面上如其所是地显现,因为人类的生存在本质上就是「形而上学的」。这在哲学传统中是绝无仅有的。海德格尔写道,「形而上学就是一种超出存在者之外的追问,以求回过头来获得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以及存在者整体的理解。」8 但是,如果此在在其存在中不是「形而上学的」,如果它的生存不是构成性地就是超越性的,作为存在者整体朝向存在的一跃,那么就这一超越是任何存在者的可领会性与显现的条件而言,这样一种追问就甚至不会划过此在的心际。在这里,形而上学不仅不是指一个学术科目,一门我们被鼓励以历史性的视角来研究的学科,而且也不是指一门科学,仅仅基于对于这一课题的理论兴趣。对存在的理解本身就是生存的一种样态,它以此在的关系行为 (Verhaltungen) 为条件,以此在闪避或坚决地承担存在,从而关联于存在的彻底实践性的——或「实践行动的」 (praxical) ——方式为条件。形而上学也是如此,因为它正是生存的一种样态。「形而上学」就是生存本身,这正是就它的超逾,它的超越性而言的,它将生存向着存在暴露出来,与存在相关联,并源始性地使生存向它本身敞开。「对存在者的超出活动发生在此在之本质中。但这种超出活动就是形而上学本身。这也就意味着:形而上学属于『人的本性』。…形而上学是此在中的一种基本发生。形而上学就是此在本身。」9
那么我们发现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同年的《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中,出现了一句几乎一字不差的相同断言。10 正如康德使形而上学成为人类理性的不可抹消的需要一样,海德格尔使它成为了生存的最深层构成。但是与康德不同的是,海德格尔并不想通过进入「科学的确定道路」来限制他的主张。相反,海德格尔从一开始便设定了思想的「严肃性」与科学的「严格性」之间的对立,他最终必定做出结论,那就是思想与科学的道路根本上就是分歧的。「所以,科学的任何一种严格性都赶不上形而上学的严肃性。哲学是绝不能以科学理念的尺度来衡量的。」11 这一谨慎而坚执的反康德主张,首先是一个反新康德主义的主张。马堡学派对于《纯粹理性批判》的「认识论」阐释正是海德格尔的首要目标。形而上学的追问是一种彻头彻尾地历史性的、内禀地有限的思想对于在其历史性中的存在本身的追问,这种追问和现代的「科学」的需求离得要多远有多远。此外,海德格尔借用康德的用语,在写给1969年译者的书信序言中断言不存在「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也就是说,不存在康德意义上的「批判」。12 质询形而上学的本质不是以现代的科学理念的尺度来限定其合法权力,而是在作为超越性的人类之生存中寻求其根基。
对无聊的分析,甚至对于畏的分析,是展示这一点的引导线索。通过这些情调 (Stimmungen) ,此在感受到自身位于存在者之整体的核心。「整体」这一表达已经含蓄地将我们带回了世界的现象中。在每一种情调中,世界本身都以一种特定的音调或「色调」——例如欢乐、恐惧或烦恼——向此在显示自身。但正如《存在与时间》强调的那样,在畏与其他大部分情绪之间存在着一个本质性的差异。在畏这里,此在的何所畏 (Wovor) 不是世界中的一个存在物,而是「世界之为世界」 (Welt als Welt) ,因为这一世界超出了一切存在物而「存在」,也就是说,它乃是关于作为超越性的生存。因此,畏的「对象」就与畏的「主体」无异: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它的何所畏与它的何所以畏 (Worum) ,它的「何所面临」 (in the face of which) 与「为何」 (for which) ,是一致的。畏是一个在存在论上存在于世的存在物在其无家可归中面对着世界本身的感受。13 或者说,畏是就此在被抛于世界,而这一被抛性就是此在之存在的特质而言,此在面对着自身的感受。这就是为什么,在这种基本情绪中——「基本」是因为它将此在带到此在本身面前,并将此在从它在常人中的遮蔽状态中移除出去——畏的对象是无处的 (nirgends) ,确切地说,它就是「无」 (nichts) ;或者说,畏的对象是「无与无何有之乡」 (das Nichts und Nirgends) ,这意味着,从现象上说,它和「世界本身」 (die Welt als solche) 是同一个东西。14 在这里,「无」这一表达意指世界本身第一次出现。海德格尔从断言畏之所关涉者是全然无规定的,并且实际上什么都不是 (nichts) 转向了另一断言,即这一所关涉者就是无、虚无 (das Nichts) ,也就是说,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世界。他将一个不定代词替换为一个名词,这将成为卡尔纳普的批判的中心点。他甚至明确地将无和世界等同起来——虚无,也就是世界本身——因此,即使最后一点没有被表述出来,虚无也被和存在等同起来,因为世界的现象源始性地植根于此在之作为在世存在的存在之中。

Leonardo santamaria丨Instagram
「形而上学是什么?」重申了这一分析的要点,它标志着其下一步。这一次,至关重要的东西在于对于「无」这一表述的意义的进一步规定,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使用这一表述的方式似乎还是未确定的。的确,为什么要谈及虚无,而不是「单纯地」谈存在呢?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畏的现象中。海德格尔指出,在畏中,存在者之整体回撤和隐退入距离之中,并如其所是地沉入无意蕴 (insignificance) 之中。但在这一回流与流波中,它们不是被消毁了。它们仅仅是在其彻底的无理由 (injustification) 中,更为有力地显现出来。在存在者隐没之际,于此显示自身的无,不能被设想为一种消毁 (Vernichtung) 的结果,而是和结构了存在论差异的「无化」 (Nichtung) 融于一体。畏使我们面对存在,这存在就是一切存在者的纯粹而单纯的他者,它本身不是一个存在者。这一「不」从本质上归属于存在。因此,无就「是」存在本身,除此以外什么都不是,或者,它就是世界之为世界这一表述中的「作为」。因此无——就它意指了世界的世界性,和存在是同一者而言——不再能被设想为否定的逻辑运算应用于被设想为「一个整体」,在其整体性中的存在者。它意指着一个积极的现象,那就是存在论差异的现象。它意味着「存在者之为这样一个存在者的源始的敞开状态」。15 或者,如同海德格尔所写的一样,「无乃是一种可能性,它使存在者作为这样一个存在者得以为人的此在敞开出来。无并不首先提供出与存在者相对的概念,而是源始地属于本质本身。在存在者之存在中,发生着无之无化。」16
海德格尔的分析是众所周知的,而我的总结的意图不是在于对它们提供一份评论。它仅仅是想要提出一个更进一步的疑问。这一疑问便在于,相对于和对立于反对虚无的批评,来思考虚无的可能性。全部问题都在于,规定海德格尔所说的东西在何种程度上是有意义的,或者说,他所说的是否仅仅是徒劳的语词游戏。卡尔纳普的目标在于更为一般的形而上学,他将其视为无意义的伪命题集合,假装具有知识的地位,而他将1929年讲座视为这种「形而上学」的完美范例。这样一来,很明显的是,他就是以一种不同于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概念的构想开始的。
打一个比方,可以说海德格尔受到了从「先验辩证论」中借来的康德的形而上学定义的部分影响,而卡尔纳普却将这一术语的意义限制在康德所说的「独断论形而上学」之上,也就是「一种完全孤立的、思辨的理性知识,它完全超越了经验的教导,而且凭借的仅仅是概念」。17 这就是定义中产生的东西,就像对于《清除》一文的简短的最后「补充」中所给出的定义一样:「这一术语用在这篇文章里,与欧洲通常的用法一样,是指所谓研究事物本质的知识领域,它超越了以经验为基础的归纳科学的领域。」18 按照这个定义,形而上学就是一门假装具有科学地位的学科,并且因此也相信它能够与经验科学竞争,因为它生产出了一种「新的知识」19 ,但却是一切经验检验所无法通达的。两年前,卡尔纳普在《世界的逻辑结构》中已经将这种所谓的「科学」界定为「科学外的理论形式的界域」 (§176) 。他在柏格森及其直观形而上学中找到了这种倾向的最佳代表。但是,他反对道,所谓的「非理性的」、「无效的」知识不可以假装具有知识的地位,因为它既不能从经验上得到证实,也不能通过经验使之失效。「没有一条路能够从理性知识的大陆通向直观的岛屿,但有这样一条道路,它从经验知识的国度通向形式知识的国度,并因而展示出来,这两个国度乃是属于同一个大陆」 (§181) 。
但对于「形而上学」的这种界定仍然是不充分的。事实上,这正是因为卡尔纳普所辩护的并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经验主义,而是一种逻辑经验主义,他的主张不仅是说,形而上学是一种伪知识,因为它位于一切验证之外;他的主张是,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也就是说,形而上学陈述甚至不能被恰当地建构为一种逻辑语言。因此,形而上学并不像康德认为的那样,建立在一种单纯的认识论幻觉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逻辑的「幻觉」之上。形而上学的陈述不仅是谬误的,没有任何知识的内容可言,因为它同经验没有任何关联,是非事实的。而且,它们是无意义的。它们「什么也没有说出来,而是仅仅表达了某种情绪和精神」。20这就是为什么事情不再像康德认为的那样,好像在清除了那些独断论的先行者之后,继续提出一种批判的形而上学是可能的。剩下的只有对形而上学遗留的问题加以纯粹内在的解决,通过一种逻辑分析的方法来暴露出它们是伪问题:这就是哲学的第一任务,如果不是它的唯一任务的话。
但海德格尔的目标是否在于,提出一种卡尔纳普在这里所理解的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也就是,一种能够和科学知识竞争的知识?换言之,卡尔纳普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不是仅仅是对一种特定形而上学的批判——那种声索「科学」头衔的形而上学?在这个程度上,它是不是依赖于它所要批判的形而上学,并且从形而上学那里借来了它的主要概念?它是不是一种以形而上学为条件的形而上学批判?反过来说,如果说海德格尔试图揭露出形而上学属于思想的范畴,而不再是属于科学的范畴,如果形而上学拒绝了「知识」的头衔,如果它所指的是人类之生存的结构化,是它在与自身的起初就是「实践性的」关系中对自身给出的阐释,如果它所产生的问题甚至不能被算作那些能够得到科学解答的问题,如果它们关系到的是每一此在居有其本己之生存的方式,以及此在尝试通过维持同这一生存的第一人称关系而使其意义透明化的方式,那么——海德格尔的事业究竟是否还处在卡尔纳普的批判的范围之内?相反,难道它不是一种属于和科学全然不同的界域的问题吗,它不能和科学竞争,但也不会陷入荒谬之中?21
大约在同一时间,维特根斯坦将这一问题称为「伦理的」。对于他来说,伦理并不构成一门关于善恶的科学,但它是「对于生活之意义的探问」。这样来理解的话,它就建立在这样一种经验之上,维特根斯坦称之为「突出的经验」 (experience par excellence) ,关于这样一种经验,他断言,「我相信,描述这样一种经验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说,当我具有这样一种经验时,我便对世界的存在感到惊异」。22 维特根斯坦接着说,这种经验将我们引导向了一个可以作为科学对象的领域,同时,它使我们达到了有意义语言的界限。他继续道,这种「将世界视作奇迹」的经验是不能以逻辑正确的语言来言说的。它使我们面对可说者的界限,它使我们「撞到了关住我们的囚笼的墙壁」。然而,他总结说,「这是一份关于人类心灵中的一种倾向的档案,我个人不禁对此抱有深深的尊重,我也不会只出于我的生活而对之加以嘲笑」。23 维特根斯坦在这里用「伦理」一词所指的东西和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非常贴近——以至于和它浑然不分。这一点在维特根斯坦与韦斯曼之间的一次对话中得到了证实,这篇对话由韦斯曼发表,它同时构成了对于卡尔纳普的事业的极其激烈的批判24:
「关于海德格尔。我当然能够看出海德格尔用存在和畏所指的东西。人有着冲破语言界限的冲动。想想这个例子,人会对任何事物存在感到惊讶。这种惊讶不能以问题的形式表达出来,它也没有解答。我们所能说的任何事情都仅仅先天地就是无意义的。克尔凯郭尔也认识到了这种冲破,甚至用几乎相同的方式描述了它(将它描述为冲破的悖论)。这种对语言限制的冲破 (thrust against) 就是伦理。我认为,伦理中是否存在知识,是否存在价值,善是否能够被定义,结束关于这些诸如此类的问题的喋喋不休,是十分重要的。」
「在伦理中,人们总是尝试说一些和问题的本质无关,也永远不会有关的东西…但是那个倾向,那种刺痛,意味着什么东西。当奥古斯丁说了这些话的时候,他就明白这件事情:『什么,无赖,你不想说出无意义吗?来吧,说一次,至少说一次,谁又在乎呢?』」
维特根斯坦不仅在解读海德格尔时表现出了非凡的洞察力;他不仅直截了当地反对任何纯粹而单纯的清除他所说的「伦理」的事业——他对于《忏悔录》1.4的自由翻译:et vae tacentibus de te, quoniam loquaces muti sunt(但谁对于你默而不言,却是祸事,因为即使这人谈得滔滔不绝,还和未说一样)25,这句话听起来就像是对于卡尔纳普的真正的侮辱,当时他本认为可以利用利用维特根斯坦的协助——而且特别是,维特根斯坦在这篇文章中强调了海德格尔的质询与实证主义计划之间的层次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得二者各自立场之间的任何平行与对话几乎都成为不可能。然而,海德格尔至少在一个关键点上与维也纳小组是一致的:伦理,尽管它对应于一种人类根深蒂固的倾向,是不可能被「清除」的,也是深深地可敬的,但是,如果不产生「无意义」,它就无法被表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海德格尔的主张仍然是与哲学格格不入的。在「伦理的」,也就是生存的维度中,不可能有关于生存的现象学。
因此,我们必须在海德格尔的陈述中,更为具体地说,在那些涉及到「虚无」的陈述中,充分地考虑意义性或意义性之缺乏的问题;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卡尔纳普的文本。

卡尔纳普的《清除》
维也纳小组的计划宣称自己是「摆脱形而上学的科学」。26 哲学只存在一个目标,那就是通过揭示科学陈述中隐含的逻辑建筑术,对科学陈述加以阐明和系统化。它不外乎是一种无内容的方法,从消极的一面来说,它使得对科学和哲学的语言中存在的逻辑谬误和无意义语词的清除成为可能,而从积极的一面来说,它「能够对有意义的概念与命题加以澄清,为事实性的科学与数学奠定逻辑的基础」。27 Überwindung,也就是「克服」,对形而上学之「克服」,抑或对其的纯粹而单纯的清除,从这一点来看,仅仅具备一个预备性的功能:它是为这样一种情形铺设下了道路,在这种情形下,哲学自己成为了一个「科学的」活动,「我希望有一天,人们不再需要发表反对形而上学的演讲。」28
为了理解「形而上学整体上」在何种程度上提出的是无意义陈述 29——并且因此不过就是伪陈述——我们必须在积极的意义上理解,为了成为有意义的,一个命题必须满足怎样的条件。实际上,这种条件是双重的: (1) 它必须在句法上是符合规则的(在逻辑句法而不是语法句法的意义上); (2) 它所包含的词汇必须自身是有意义的。我们将会看到,第二个准则仅只适用于综合的陈述,也就是说,它仅只适用于那些不仅就它们的形式而言是真的,而且就它们与经验的关联而言也是真的陈述。
从这种类型学中产生出了两种伪陈述的范畴:第一种伪陈述中有一个或更多语词(变项和宾词,它们与逻辑连接词和量词不同)是无意义的;第二种伪陈述从句法上看是不融贯的,对于这种陈述的任何逻辑上的释义都是不可能的。卡尔纳普在他的文章的第二、三部分考察了前者,而在第四、五部分考察了后者。
在讨论卡尔纳普对这两种无意义的分析之前,有必要揭示逻辑实证主义意义学说的主要内容。按照维也纳小组的观点,一切命题要么是分析的,要么是综合的。分析命题是一种同义反复,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出于其形式而必然为真的陈述。举例来说,「要么在下雨,要么就不在下雨」,这句陈述对于目前的天气状况就没有说出任何东西。它没有经验性的内容,没有指称世界中的任何事实,仅限于说明了在对连接词「要么」的使用中起支配作用的句法规则:当「要么」连接的两个表达中至少有一个为真时,包含这个连接词的命题就为真。对于卡尔纳普而言,和维特根斯坦一样,逻辑学和数学的命题都在这个意义上是分析的。它们是重言式,或者对于重言式的重言式转换。在这些命题这里,理解它们的意义和理解它们是仅仅出于其形式便为真的,也就是说,理解它们是同义反复的,是一个意思。在第二种命题那里,事情便有所不同了;这些命题是否为真取决于一个非语言的标准:它们所指称的经验。如果它们所指称的事态存在,它们就是真的,而如果那种事态不存在,它们就是假的。但是要想能够成为真的或是假的,它们必须首先是有意义的。在这里,真的问题和意义的问题是有所不同的,这与分析陈述的情况相反。30 如果陈述是真的,它就是有意义的,但它有意义并不意味着它就会是真的;出于其内容,它也可能是假的。那么,在何种条件下,一个综合陈述才能是有意义的?这在维也纳小组看来是一个基本问题,因为它引导我们将科学陈述(或者那些能够成为科学陈述的陈述)和非科学陈述(和那些无法成为科学陈述的陈述)区分开来:后者就是形而上学陈述。

Leonardo santamaria丨Instagram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逻辑经验主义看来,每一个问题都只有一个解答——如下:如果一个综合陈述和经验有一种确定的关联,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陈述能够符合于可验证或可失效的事实,它就是有意义的。在逻辑实证主义的框架中,这个经验的标准要叠加一个严格的形式标准,后者能够推论性地确定那些陈述是有意义的,而哪些则不是:一个综合陈述是有意义的,当且仅当它能够从观察得到的陈述所组成的有限集合中推导出来。这一标准假定,首先,一个综合陈述必须从句法的角度上说是形式完善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它就无法从任何其他陈述中推导出来。其次,这意味着必须能够从一个综合陈述中推导出一类更为简单的陈述,直到我们推导出可以直接地得到验证的陈述,或者所谓的「规约陈述」 (Protokollsatze) ,因为这些陈述提供了经验或观察的规约,对于这些陈述的验证使得验证所讨论的陈述成为可能。举例来说, 「x是节肢动物」这一命题是有意义的,如果它能够从这类观察性的陈述中派生出来的话:「x是动物」,「x有有关节的腿」,「x有分段的身体」,「x有几丁质外壳」。31 那么我们就能建构出如下的推论:「如果x是一个动物,且有有关节的腿、分段的身体和几丁质外壳,那么x就是一个节肢动物」,这就为「节肢动物」一词的意义提供了一个标准。在这里,我们就有了一个判断语词意义的纯粹形式的,因而也是客观的标准,它完全独立于我们通过这个语词所「意指」的是什么——它具有什么样的心灵表征,使用它会联系到什么样的情感——这个心理学问题。简言之,我们就可以为一个综合陈述的意义提供如下一般定义:「一个陈述的意义就是验证这一陈述的方法」(石里克)。
如同卡尔纳普所称呼的那样,这种逻辑上的「还原」 (Zurückführung) 32 程序也就使得通过揭示形而上学陈述的第一类无意义——关于词汇的无意义,而非逻辑句法上的无意义——而清除它们成为可能。出于一些原因,我们几乎没有必要坚持卡尔纳普的论证的这个方面。首先,他的这部分论述完全附属于验证的意义理论,这种理论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33,不久也被卡尔纳普在《语言的逻辑句法》§34中所抛弃。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仅仅有学说志 (doxographical) 上的兴趣。其次,即使我们仅仅考虑它应用于对形而上学陈述的批判这一情况,这一学说也变得惊人地混乱和专断,它被它的各种预设破坏了。其中最为幼稚的大概莫过于断言称每一个语词被引入语言当中「没有别的目的,它的目的仅仅在于表达某物」,它必须「从开始使用它起」就有一个确定的意义。34 按照这种看法,仅仅是随后,「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意义才开始发生波动。形而上学不外乎就是在玩弄这个语义上的不确定性:在形而上学中,「语词被剥夺了它们早先的意义,而没有被给予一种新的意义」,而先前和语词联系在一起的心理图像现在则被「新的心理图像和感受」所取代35;形而上学就这样发明出了「伪概念」。按照这种亚当式的语言学说,语言最初是由完美的单义意义所组成的,它只是随后才被哲学的巴别塔所扭曲了。卡尔纳普不仅从没有证实这一断言(给予他自己的原则,这又如何可能?),并且这一断言也导致了显而易见的错误。说明这一断言的例子,「αρχή」一词,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卡尔纳普认为,这个词有着一个「原初的意义」,也就是「开始」,然后这个词被从使用中抽离出来,被哲学加以隐喻性的使用。但是,只要翻开一本词典就足够了,我们会看到「αρχή」从荷马时代起就有几种不同的主要意义了。36 此外,卡尔纳普的主张不仅是错的;它通过分析也被证明是完全不清晰的。第二个例子,「神」一词,就展示了这一点。按照卡尔纳普的说法,这个词有三个,并且只有三个,相互区别的用法: (1) 神话的——在这种情况中,它涉及的是「奠居于奥林匹斯山之上的物理存在者」,它们偶尔会向人显示自身,因而是「经验上可观察的」37; (2) 形而上学的——在这种情况下,「神」不指称任何可观察的东西;因此它产生了一个「伪概念」; (3) 神学的——卡尔纳普坚持认为,第三种用法不断地在前两种用法之间「摇摆」。我们怎样看待这种分类呢?首先,声称从形而上学家(附带地还有神学家)的角度来看,不可能存在对于上帝的经验,这完全就是错误的;甚至不用提神秘主义的经验,神学是接受荣福直观 (beatific vision) 的可能性的,而且形而上学也会区分对于神圣者的经验的许多样态:例如,亚里士多德对于第一推动的沉思,抑或是笛卡尔关于无限的观念。这些「经验」可能算不上经验;但这一点必须首先得到确证。但现在,卡尔纳普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他所否认的,就不是「神」一词具有一种意义,而是首先,并且更为基本地来说,存在着一种一般的对于神的可能的经验,也就是说,他否认了任何像「神」这样的东西是存在的。这种主张被称为「无神论」。但它涉及到的是哲学(或形而上学)命题,而不仅仅是一个逻辑上的澄清。如果对于神的经验是不可能的,那毫无疑问,许多形而上学的领域就是全然无意义的,但它的缘由和卡尔纳普给出的完全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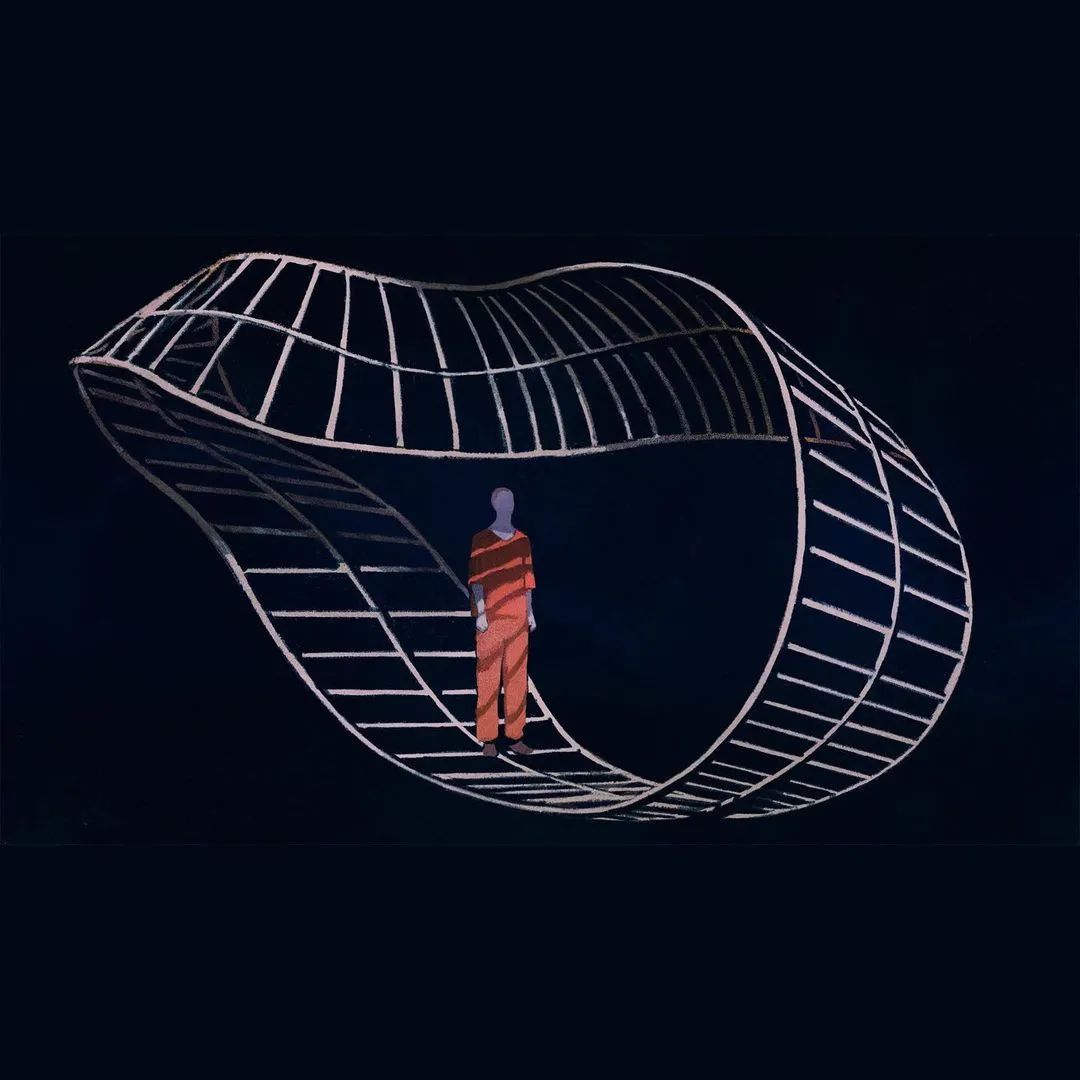
Hokyoung Kim丨Instagram
不过这可能不是重点。的确,无论批判的这第一个部分重要性如何,我们仍然需要考察卡尔纳普认为自己能够揭示出来的第二种类型的形而上学无意义,在他看来,这显然是最严肃的:逻辑句法上的无意义。海德格尔关于虚无的文章就属于这一范畴,但在讨论这一点之前,我们必须再一次简短地离题。
在开始讨论海德格尔的问题之前,卡尔纳普为我们给出了这种范畴的无意义的一个范例,他声称这是来自罗素的类型论:「凯撒是一个质数」。他说,这个命题便接近于形而上学命题,因为尽管它遵循了英语的语法句法,但它从逻辑句法上说是不融贯的。它将一个只能接纳数字的名称的数字宾词应用到一个人的宾词之上:简言之,它将隶属于不同的逻辑领域的名称和宾词混合在了一起。我们可以诉诸类型论来确证这一断言吗?38 不能,因为类型论是一种严格的句法理论39,确定卡尔纳普所说的「不同的逻辑领域」的含义,而不诉诸语义上的考量,这是不可能的。但问题还在于:卡尔纳普认为「凯撒是一个质数」这一命题在句法上是不融贯的,这一断言必然导致一个悖论。事实上,如果事情就是如此,对这一命题的否定必然也是不融贯的。那么,如果我们认为「凯撒」命题在罗素的意义上是一个确定性描述,它的否定就是这样的:「要么有一个x,x是凯撒,而x不是质数,要么有一个x,x是凯撒且x是质数是错的」。这个否定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还是真的。因此,质疑「凯撒是一个质数」这一命题是不是仅仅简单地为假,而不是像卡尔纳普认为的那样,是「无意义的」,这样做似乎至少是合理的。

句法无意义与虚无的疑难 但是,这些评论并没有完全削弱卡尔纳普对于形而上学无意义的分析以及他对海德格尔的批判的尖锐性。首先,我们要怎样理解这个「形而上学无意义」?正如我所坚持的那样,这不再是「由于不可验证和缺少内容而不具备意义的陈述」40,而是这样一类陈述,它构成了对于逻辑句法本身的违犯。尽管在语法上,这些陈述是正确的,但它们无法以「一种逻辑上无误的语言」表达出来。41 总而言之,形而上学家在这里就是被自然语言的表层语法所迷惑,而他对深层语法的理解却是错误的。卡尔纳普确立这一点的策略是绘制了一张表格,这张表格能够使读者在三种表达中进行联系与比较,它们分别是从普通语言(第一栏)中借用而来的表述、海德格尔文本中的表述(第二栏)——这些表述通常是残缺不全的并脱离了语境——以及最后,以由一阶谓词逻辑的形式化语言写成的「逻辑无误」的表述(第三栏)。这一操作的目的何在?其目的在于,展示出海德格尔的陈述和普通语言陈述相反,它们不可以被转写为任何恰当的逻辑释义。但这还不是全部。如果问题仅仅在于认识到如何对海德格尔的表达做出释义——特别是那些用于虚无的表达——那么提及日常使用中「外面下雨了」,「我们知道雨」这样的表达就会是多余的。如果卡尔纳普提及了这些表达,那是因为他的目标不仅在于揭示海德格尔表达中的逻辑不融贯性,而且首要地还在于,展现出这些表达的形而上学特征。那么,为了确立后一点,就有必要展示海德格尔的表达是如何来源于日常使用,并且又是如何从日常使用中转移出来的。
因此,从一开始,卡尔纳普的论证中就显露出一种张力。乍看起来,他的论点似乎是这样的:海德格尔认为他是在根据语言的日常使用来运用语言,但这样一来,他就使自己被语法句法所迷惑,并对深层句法产生了错误的理解。但如果这真的只是「错误」的话,它们就应当是可以被纠正的。那么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如此反驳卡尔纳普:这些错误是偶然的,它们也不是一些特别重要的事情,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些错误和他所说的「形而上学」都没有什么关系可言。卡尔纳普因而被他的论证的逻辑所迫而更进了一步。他必须确立的一点是,海德格尔不仅对「虚无」一词的使用产生了误解,而且他有意以偏离日常使用的方式来对该词加以运用,而由于这种日常的使用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他这样做也就有意地违犯了语词的逻辑句法:卡尔纳普写道,「论文的作者非常清楚他的问题与陈述之间存在冲突。」42 但卡尔纳普针对这一点提出了自己的反驳,海德格尔有意地违犯了日常使用,因为他没有按照语词的日常使用来对待它们。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装作要纠正他就会是毫无意义的,正如卡尔纳普被迫认识到的一样:如果「『虚无』一词在海德格尔的论文中具备一种意义,这种意义和习惯上的意义又完全不同的话…那么ⅡB句中提到的逻辑谬误就不会发生。」43
如此一来,卡尔纳普便走投无路了:他提出了两种对于海德格尔的批判,但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这两种批判彼此之间是不相容的。一方面,他强调海德格尔是在习惯性的、前哲学的意义上使用诸语词的。因此,当我们使用「虚无」一词时,他表达的不外乎就是一些这样的句子中所说的东西,例如「在外面一无所有」,这种句子能通过一种否定的存在量化而在一阶谓词演算中得到释义。在这种情况下,海德格尔仅仅是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因为他不具有把「没有」 (nichts) 替换为「虚无」 (das Nichts) 的权利。为了造成这一替补,他便放任自己被语法所迷惑,因为他在「将『虚无』一词作为一个名词来使用」。44 另一方面,这个错误又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无思想性的错误;它必须揭示了一些关于形而上学之事业的事情,那就是对于逻辑的系统性违犯。于是海德格尔被指责为有意地触犯了语言的深层句法。为了有助于这种阐释,卡尔纳普可以引用海德格尔的那篇讲座,在其中他攻击了哲学中逻辑的至尊性。卡尔纳普总结道,海德格尔的疑问与问题,「同逻辑的、科学的思考方式相抵牾」。45
但卡尔纳普不是不得不做出选择吗?海德格尔要么是有意地违犯了句法,要么就是放任自己被语法所迷惑;他要么是在习惯意义上使用语词,要么就是赋予了它们新的含义,这样也就排除了逻辑转写的可能性,而逻辑转写是要将它们处理为同日常语言在语法上相似的例句。要么是逻辑转写揭示了种种错误,要么是海德格尔以这样一种方式使用了语言,通过这种方式,他有意地拒绝了对于他所说东西的任何逻辑转写。而实际上,卡尔纳普必须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做出选择,因为这个最后场景使得他的批判变得不得要旨。如果海德格尔的确丝毫没有将同日常语言相类似的那些陈述来作为他的陈述的模型,如果他是在同日常含义完全相异和无关的意义上来使用诸种语词,从而如果他拒绝了逻辑转写的原则,因为这种原则会使得他的命题与日常语言中的命题毫无二致,那么卡尔纳普的批判就失去了一切承载力;这个批判就会是无对象的、多余的,甚至是荒诞的。
因此,为了使自己成为有意义的,卡尔纳普的批判必须不断地在两个不相容的断言之间摇摆不定。海德格尔必须是在日常语言中言说的又不是在日常语言中言说的;他必须言说一种非形而上学的语言,又必须持续且有意地僭越它;他必须既是可纠正的又不是可纠正的,如此等等。但实际上,由于第二个假设导致了卡尔纳普的批判的崩溃——因为如果它是正确的,「ⅡB句中提到的逻辑谬误就不会发生」46——唯一的选择便在于回到第一个断言那里去。这正是卡尔纳普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但是这一节开篇所引用的第一句话证明了这种解释是不可行的。『唯有』和『别无其他』 (nothing else) 这两种表述的结合明白地告诉我们,在这里,『虚无』一词有着逻辑助词所具备的通常含义,它乃是用于表述一个否定的存在陈述。于是引入『虚无』一词立即就导向了论著中的那一主导问题:『这个虚无是怎么回事?』」47
这一论证极端地孱弱,这至少出于三个理由:首先,它假定,从一个语词曾经在「习惯性」意义上被加以使用的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结论,认为继此以后它都总是且必然是在相同的意义上来使用的。正如詹姆斯·科南特所发现的一样,这一断言违反了卡尔纳普在《算数基础》中一开始所提出的语境原则。一个语词只有在命题的语境中才是有意义的,而对虚无一词的出现场合加以考察并不足以从整体上将该词出现于其中的命题使用它的法则确定下来。
其次,最重要的是,海德格尔是在习惯性意义上使用诸语词的,因而「虚无」一词对于他来说就「有着逻辑助词所具备的通常含义,它乃是用于表述一个否定的存在陈述」,这一断言与文本本身的证据是矛盾的。的确,海德格尔在「无」一词的代词和状语性使用以及名词化使用之间做出了区分。此外,他也不是第一个做出这一区分的人:首先,德国语法本身就做出了这一区分。如果是海德格尔的语言在不定代词和首字母大写的名词之间标识出一种差异,那又怎么可能是海德格尔让自己被他的语言所迷惑呢?海德格尔怎么可能会将「虚无」一词的逻辑句法与语法句法混淆起来,既然「没有」和「虚无」之间的差异在德语的语法层面上,在书写这些语词的方式中就已经被标识出来?
最后,卡尔纳普的论证又遭到了一种反驳,即「虚无」这一名词,无物、虚无,在日常语言中并没有使用,它仅仅是一个严格的哲学(或神学)词汇。很难看出来,在这些情况下,要怎样使用它才能是任何「错误」——无论它是什么——所致的后果。总而言之,卡尔纳普归咎于海德格尔的「错误」,也即将「没有」一词当作一个对象的名称,因为「『虚无』一词有着逻辑助词所具备的通常含义,它乃是用于表述一个否定的存在陈述」48,这绝不是一个错误,也不能是一个错误,因为这一表达在日常语言中完全不是以名词形式来使用的,这个名词形式是形而上学家赋予它的。至于海德格尔事实上是否将这一表达用作一个对象的名称,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暂且搁置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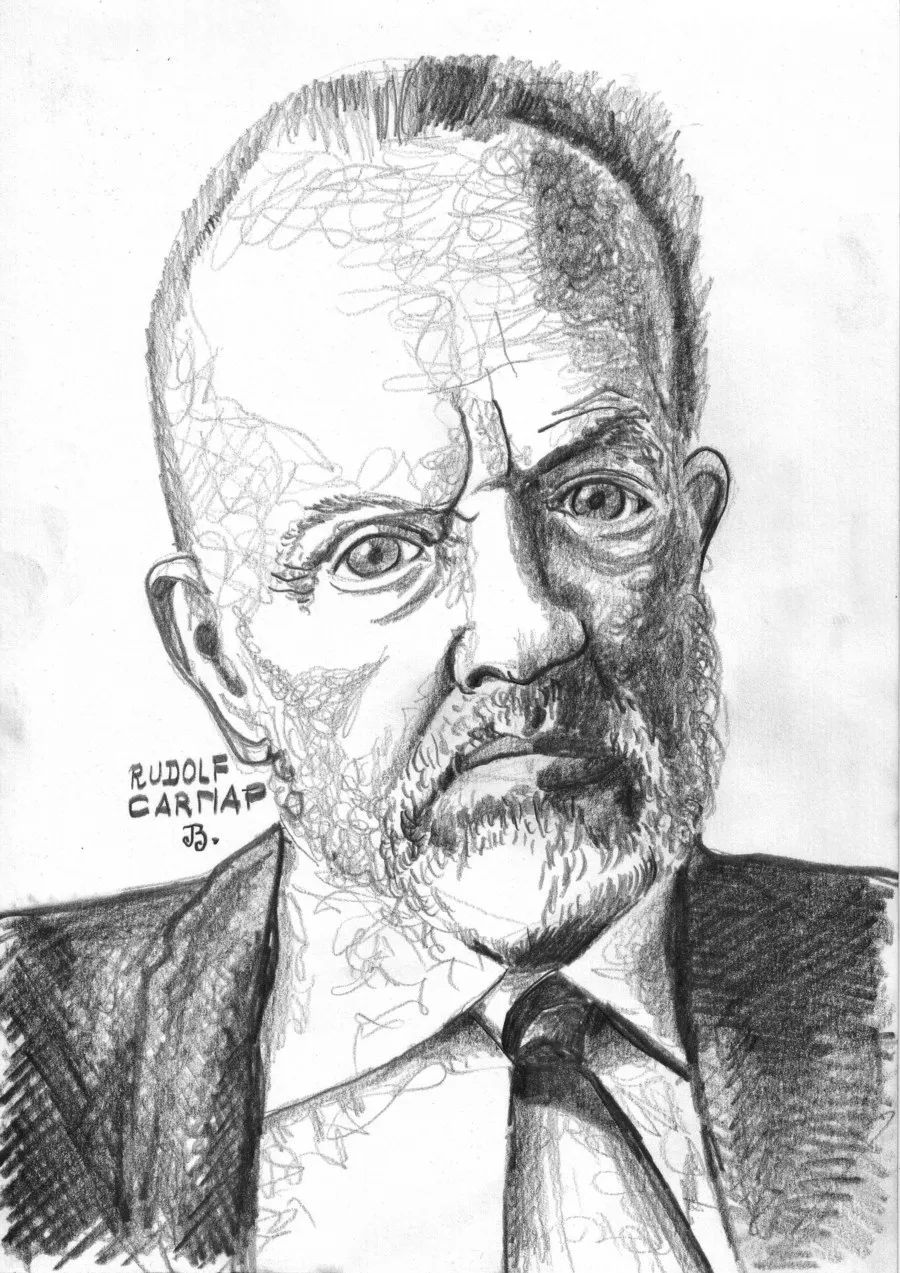
鲁道夫·卡尔纳普 (Rudolf Carnap) 丨Typepad
事实在于,卡尔纳普非但没有对海德格尔的陈述加以忠实的诠释,他还有意地在「形而上学是什么?」的文本中引入了一个「错误」,来服从于他的目的。不顾文本的内容为何,他先天地决定了,海德格尔只能用「虚无」表示日常语言用「没有」在「外面一无所有」这类句子所表达出的含义,也就是「在外面没有东西」。因此他又决定,海德格尔的陈述可以被合法地转写为否定存在量化。因此,卡尔纳普不仅废除了海德格尔不断在虚无与一无所有之间做出的区分,而且通过提出这样的转写,他就使自己陷入了矛盾。为了使自己能够前后一致,卡尔纳普应该说,「对于海德格尔所使用的『虚无』一词,我并不理解任何东西,因为这个词不能在一阶谓词逻辑中得到转写。」但这恰恰不是他所说的东西。相反,他说,「我完全理解海德格尔用Nichts所表达的东西,他表达的正是日常语言用不定代词nichts所意味的同一个东西,但我所完全了解的、可以被如此地转写下来的东西,我却不理解它,也不能对它提供一个转写。」
此外,同卡尔纳普本人对海德格尔的用语给出的转译相反(它们被临时转换为了断言,因为只有断言才能为真或为假,唯独它才能具有一种满足卡尔纳普的标准的意义),诸如「外面寻求虚无」、「我们发现虚无」这样的用语,卡尔纳普被迫承认,在海德格尔对「虚无」一词的实际使用中,「虚无」完全不是在和「没有」(对于存在量化的否定)相同的意义上得到使用的,它很明显是一个名词。卡尔纳普认为他有权由此得出结论,那就是这个名词是一个对象的名称:「因为即使我们容许将『虚无』作为一个存在物的名称或描述,这个存在物的存在按照定义也会遭到否认,但句3(『虚无存在仅仅是因为…』)却继续承认了它的存在。」49在这里,卡尔纳普向海德格尔提出了他的全部批判中唯一一个融贯的论证,但这个论证也是最为传统和陈旧的,某种意义上说,形而上学反对言说虚无的可能性,这一论证的首次表达可以追溯到巴门尼德本人那里。如果每一个名词都必须有一个指称物,又如果具有一个指称物就意味着要指称一个对象,那么「虚无」这个词用作名词就必须指称某物,指称一个对象:虚无。而虚无又是对于一切对象的否定。因此「虚无」一词就绝不能被用作一个名词。我们还有机会回到这个问题。就目前而言,表达出两个疑问就足够了:每一个名词都必然是一个对象的名称吗?虚无必然是对于任何对象的否定吗?
海德格尔看出了这里有一个问题,于是他将这个问题直接表达出来。在他的《尼采》第二卷中,海德格尔还概述了一份回应——不无讽刺地。「作为对于任何『客观』之物的『否定』,就其自身而言,虚无不『是』一个可能的对象。谈论虚无并在思想中追求虚无,这被展现为『无对象的』计划,空洞的语词游戏,此外似乎还没有提及这些计划总是直截地自相矛盾,因为无论它们如何对无加以规定都总是不得不去说虚无是这样那样的。」现在来评估这一回应的价值还为时过早,它对「对象」的逻辑概念——和形而上学概念——的适切性与重要性提出了质疑:我们将会返回到这一点上来。
至于卡尔纳普提请我们注意的后一种「无意义」,无需给出额外的评论。在他看来,「无无化」当然是所有无意义中最严肃的一种,因为它在句法的无意义之上又增补了一种词汇上的无意义。它制造了一个新的动词,「无化」,很容易看出这个词汇并不满足卡尔纳普的标准。「引入了一个新的语词,但却没有一个初始的意义。」但「初始」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卡尔纳普是在说,一切新语词,恰恰由于它们是新的,它们就是无意义的吗?当然不是。他是说唯一有意义的新语词是这样一些语词,关于它们能够指示一种验证方法,从而补充了科学的词汇。但是日常语言创造新词汇是为了将来的某一天将它们纳入科学的词汇表之中吗?坚持这一点是无用的。如果海德格尔使用他的语词「用的是和其他地方全然不同的一种意义」,事情就不是这样了,卡尔纳普这句话同时表达了两个意思:这种用法不同于日常使用(这是平凡的),以及它预先排斥任何可能的逻辑释义。但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卡尔纳普的论证就会崩溃;因为海德格尔的用语就不再包含他所指出的那些错误。
但事实上问题是不是并不在这里?我们难道不是竟然必须坚持认为海德格尔对「虚无」一词的使用会导致他——假设这个问题对于他来说能够产生真正的兴趣的话——拒绝以现代符号逻辑语言来对它进行任何逻辑转写吗?「形而上学是什么?」讲座完全致力于攻击「哲学中『逻辑』的统治」以及一切形式的实证主义。在这一方面,与其说是卡尔纳普在1931年对于「目前在德国有着最大影响力的形而上学学派」发起了敌对;不如说,是海德格尔本人在两年前以隐晦的言辞攻击了逻辑实证主义52——卡尔纳普的文章可以被阐释为一个回应。顺便说一句,海德格尔在其讲座的一条边注中指出,在这篇文章中得到处理的,是科学通过主张自己要处置的是存在物「而别无其他」,从而排除了虚无之疑问的方式,这个表述是他从丹纳那里借用来的,而丹纳是一名实证主义者。海德格尔就此以出色之至的明晰性重申了他针对逻辑-数学之对于他所说的「虚无」的形式化提出的反驳:在关涉于存在(因而也关涉到虚无)之时,「我们不希望捕捉到以形式思维的形式图示在这里所打开的东西。」53
但这样一道防线的价值何在?它难道不是削弱了采取这种方式的人吗?事实上,一种拒绝对自身之断言进行任何逻辑转写的思想究竟是什么?毕竟,难道我们不是达到了某种这样的理念,除了将它认作一种「非理性主义」以外就再没有别的理解它的方式?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为确定的了。相反,如果我们理解了它的含义——特别是理解到这一点,即对逻辑的批判本身并非专断任意的,它不是某种个人偏好或任何类型的意见的结果,而是奠基于对那种在哲学上得到意义之探问的学说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分析之中——这种防守或许就是十分强有力的。在澄清海德格尔所谓的「非理性主义」所开启的违逆之前,我们必须询问一个预备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是本身就已经参与到了我们所反对的这一非理性主义当中的话。海德格尔对于数学逻辑及其优先性的拒斥在哲学上意味着什么?主张凭借弗雷格和罗素的逻辑形式主义的标准来评定他的断言的意义之有无,海德格尔对于这样一种事业的驳斥意义何在?
(未完待续)
注释与参考文献:(滑动查看更多) [ 1 ] 引自《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7页——译注
[ 2 ] Henri Maldiney, Ouvrir le rien, l'art nu (Fougeres: Encre Marine, 2000), 113
[ 3 ] Heidegger, Was ist Metaphysik?, in Wegmarken, GA 9: 106. (中文引自《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第123页——译注)
[ 4 ] 《路标》,第125页——译注
[ 5 ] Ibid., 107, 117. (《路标》,第136页——译注)
[ 6 ] Bertrand Russell, Our Knowledge of the External World as a Field for 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soph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14), chap. 2.
[ 7 ] Rudolf Carnap, "The Elimination of Metaphysics through Logical Analysis of Language," trans. Arthur Pap, in Logical Positivism, ed. A. J. Ayer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9), 60-81.
[ 8 ] Heidegger, Wegmarken, GA 9: 118. (《路标》,第138页——译注)
[ 9 ] Ibid., 121-22. (《路标》,第141-142页——译注)
[ 10 ] 参见Heidegger, 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 GA 3: 231:「形而上学是此在中的一种基本发生。形而上学就是此在本身。」
[ 11 ] Heidegger, Wegmarken, GA 9: 122. (《路标》,第142页——译注)
[ 12 ] 康德在与马库斯·赫兹的信 (大约1781年5月11日) 中的言论,收于Philosophical Correspondence, 1759-99, ed. and trans. Arnulf Zwei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95。
[ 13 ]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188.
[ 14 ] Ibid., 186-87. (中文引自《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第263页——译注)
[ 15 ] Heidegger, Wegmarken, GA 9: 114. (《路标》,第133页——译注)
[ 16 ] Ibid., 115. (《路标》,第134-135页——译注)
[ 17 ]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Ak. III.11. (中文引自《康德著作全集第3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9页——译注)
[ 18 ] Carnap, "Elimination of Metaphysics," 80.
[ 19 ] Ibid., 72.
[ 20 ] "The Scientific World Conception" [对于一本匿名小册子"Wissenschaftliche Weltauffassung"第二部分的翻译], in Empiricism and Sociology, by Otto Neurath, ed. Marie Neurath and Robert S. Cohen (Dordrecht: Reidel, 1973), 307.
[ 21 ] 此外,卡尔纳普也承认存在着他称之为「生活之谜」 (Lebensrätsel) 的东西,但他拒绝承认它们具有问题的地位;参见Carnap, 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 (Berlin: Welkreis-Verlag, 1928), §183。
[ 22 ] 分别为Ludwig Wittgenstein, "A Lecture on Ethics," Philosophical Review 74, no. 1 (January 1965): 5, 8, 8。
[ 23 ] Ibid., 11, 12.
[ 24 ] 1929年12月30日的对话,收于Philosophical Review 74 (1965): 3-27。不包含第一句话 (引用了海德格尔) 和最后第一段。关于这一比较,同样参见Franco Volpi, "Wittgenstein et Heidegger: Le 'dépassement' de la métaphysique entre philosophie analytique et philosophie continentale," in La métaphysique: Son histoire, sa critique, ses enjeux, ed. Jean-Marc Narbonne and Luc Langlois (Paris: Vrin-Laval, 1999).
[ 25 ] 中文引自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第6页——译注
[ 26 ] "Scientific World Conception," 305.
[ 27 ] Carnap, "Elimination of Metaphysics," 77.
[ 28 ] Carnap, "Uberwindung der Metaphysik," 1932年12月于布尔诺发表的演讲,由Michael Friedman引用,收于A Parting of the Ways: Carnap, Cassirer, and Heidegger (Chicago: Open Court, 2000), 19。
[ 29 ] Carnap, "Elimination of Metaphysics," 61.
[ 30 ] 参见Maurice Clavelin, "La premiere doctrine de la signification du Cercle de Vienne," Etudes philosophiques 4 (October-December 1973): 475-504。
[ 31 ] Carnap, "Elimination of Metaphysics," 63.
[ 32 ] 关于还原作为派生的逻辑程序使建立语词的意义成为可能,参见Carnap,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 §2。
[ 33 ] 关于部分意义显著的批评,参见Russell, "Logical Positivism," in The Philosophy of Rudolph Carnap, ed. Paul Arthur Schilpp (La Salle, Ill.: Open Court, 1962)。关于一份更一般的介绍,也参见Pierre Jacob, Logical Empiricism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80)。
[ 34 ] Carnap, "Elimination of Metaphysics," 62.
[ 35 ] Ibid., 65-66.
[ 36 ] 《拜利希腊语法语词典》列出了下列主要意义: (1) 开端,本原,起源; (2) 命令,权力,权威。在卡尔纳普看来,「起源」 (origin) 的意义就是哲学对该词的隐喻性使用的一个典型例子,但这个意义被证实在荷马史诗中出现了数次:例如,在Iliad 22.116中,αρχή νείκεος的意思不是「争吵的开始」,而是「争吵的起因」;在Odyssey 21.4中,αρχή φόνος也不能被翻译成其他意思,它的含义是「凶杀的起因」。
[ 37 ] Carnap, "Elimination of Metaphysics," 66.
[ 38 ] Ibid., 75.
[ 39 ] "Difference of type means difference of syntactical function" (Russell, "Reply to criticism," in The Philosophy of Bertrand Russell. ed. Schilpp (New York: Tudor, 1951), 692; quoted by Ali Benmakhlouf, in Bertrand Russell: L'atomisme logique (Paris: PUP, 1996).
[ 40 ] "Scientific World Conception," 308.
[ 41 ] Carnap, "Elimination of Metaphysics," 69.
[ 42 ] Ibid., 71.
[ 43 ] Ibid.
[ 44 ] Ibid., 70.
[ 45 ] Ibid., 72.
[ 46 ] Ibid., 71.
[ 47 ] Ibid.
[ 48 ]James Conant, "Two Conceptions of Die Oberwindung der Metaphysik: Carnap and Early Wittgenstein," in Wittgenstein in America, ed. Timothy McCarthy and Sean C. Stid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1), 34.
[ 49 ] Carnap, "Elimination of Metaphysics," 71.
[ 50 ] Ibid.
[ 51 ] Heidegger, Nietzsche II, GA 6.2: 41.
[ 52 ] Carnap, "Elimination of Metaphysics," 71.
[ 53 ] Heidegger, Wegmarken, GA 9: 117.
[ 54 ] Carnap, "Elimination of Metaphysics," 69.
[ 55 ] 1929年3至4月,海德格尔在达沃斯结识了卡尔纳普;此后他们进行了一些哲学上的交流。3月30日,卡尔纳普在他的日记中提及他们一起出去散步,途中他们探讨了「新的存在问题」。4月3日,他们在一家咖啡厅讨论了「以物理术语表达一切事物,甚至是意向和意义的疑问的可能性」 (这一问题在接下来数年间占据了维也纳小组的讨论话题,卡尔纳普和纽拉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便证实了这一点) ;参见Michael Friedman, Parting of the Ways, 19。让我们回想一下,「形而上学是什么?」的讲座是在1929年6月24日于弗赖堡发表的——这是在进行对话的三个多月之后。
[ 56 ] Heidegger, Wegmarken, GA 9: 105, note (a).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Philosophia 哲学社
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备战深国交网”除发布相关深国交原创文章内容外,致力于分享国际生优秀学习干货文章。如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原谅,并联系微信547840900(备战深国交)进行处理。另外,备考深国交,了解深国交及计划参与深国交项目合作均可添加QQ/微信:547840900(加好友时请标明身份否则极有可能加不上),转载请保留出处和链接!
非常欢迎品牌的推广以及战略合作,请将您的合作方案发邮件至v@scieok.cn本文链接:http://www.scieok.cn/post/2545.html
-
<< 上一篇 下一篇 >>
虚无现象学是否可能?卡尔纳普与海德格尔的争辩 (上)/ 翻译
40871 人参与 2021年11月17日 13:22 分类 : 深国交哲学社 评论
search zhannei
深国交2024年英美本科录取小计
-

未标注”原创“的文章均转载自于网络上公开信息,原创不易,转载请标明出处
深国交备考 |
如何备考深国交 |
深国交考试 |
深国交培训机构 |
备战深国交 |
联系方式
Copyright www.ScieOk.cn Some Rights Reserved.网站备案号:京ICP备19023092号-1商务合作
友情链接:X-Rights.org |中国校园反性骚扰组织 | 留学百词斩 | 南非好望角芦荟胶 | 云南教师招聘考试网 | 备战韦尔斯利网| 备战Welles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