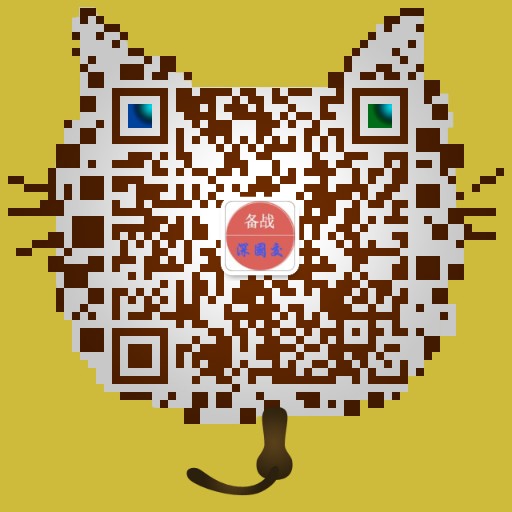当前位置:首页 » 深国交哲学社 » 正文
-
本文译自2017年的《政治悲观主义:卡尔·施密特、米歇尔·福柯和吉奥乔·阿甘本的消极的世界建构与政治行动的(不)可能性》(Politischer Pessimismus Negative Weltkonstruktion und politische Handlungs(un)möglichkeit bei Carl Schmitt, Michel Foucault und Giorgio Agamben) 的第八章「综观:政治悲观主义」。
作者 / Jan-Paul Klünder 翻译 / fwat 排版 / 亦源
本书中的研究旨在说明卡尔·施密特、米歇尔·福柯和吉奥乔·阿甘本的写作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某种政治悲观主义的特征。为此,我先定义了政治悲观主义在理想状态下具有的典型范畴:1.走向衰落的历史 (Niedergangsgeschichte) ;2.古今对比的衬托;3.悲观主义的人类学;4.悲观主义的历史哲学;5.对未来的预言;6.悲观主义的态度以及表现,并藉由这些范畴分别对三者的理论进行了分析。最后,这种统一的方法提供了横向比较的视角,以简明扼要地指称及阐释施密特、福柯和阿甘本三者对现代社会的观察的异同。 在迄今为止的章节中可以看出——正如在开头所猜想的那般,施密特、福柯和阿甘本都消极地描述了现代社会的发展。现在,我们则可以区分开这三种对于所谓衰落的不同的认识。首先,施密特既反对宗教改革也反对世俗化,同时对于专制国家形式的时代给予了积极的描述。施密特认为,在欧洲,国家形式的政治秩序早在法国大革命的进程中即已受到了侵蚀。所谓由此产生的窘境,在他对于 20 世纪所开展的激烈的文化批判里已有体现。同样,福柯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历史调查也一直关注现代性的阈限、从 18 世纪到 19 世纪的过渡,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种种变动,尽管对于福柯而言,施密特的批判的观点仍显陌生。福柯并没有 (即使是在表面上也没有) 描述「去政治化和价值中立化」的进程,而是描述了「规训化和规范化」(Disziplinierung und Normalisierung) 的进程;正是通过这个进程,主体作为他自己的可能性的条件 (als Bedingung ihrer Möglichkeit) 而屈服于权力关系。福柯尤其如此表明了被期待已久的人的解放是如何被颠倒为其反面的;藉此,福柯并非是要描述任何一个腐朽社会的衰落,而毋宁说是描述理性自身的消极的进程。施密特认为,正是理性和人权的普世主义 (Universalismus von Vernunft und Menschenrechten) 导向了无限贬低敌人的战争概念、敌意的不断升级,以及战争的传统边界的消解。福柯则认为,在启蒙的过程中产生了种种制度和话语,而它们的权力技术则在微观层面上渗透到整个社会体和每一个个体之中。 
德国法学家,政治学家卡尔·施密特 相比之下,阿甘本的现代性批判并没有选择现代性的阈限作为起点;他用《神圣人》(Homo Sacer) 的一整个系列来解释,由于bios和zoe之间的原初区分,生命在古典时期就已被交由主权而赤裸得毫无防备可言。自此盛行的包容着的排斥 (einschließenden Ausschluss) 的逻辑则在 20 世纪愈发抬头,同时,集中营形式的例外状态则反而成为正常的行政实践。阿甘本的诊断与他的文化批判相辅相成:他在其中谴责了「景观社会」并揭露所谓的「经济的范式」对人的全面宰制。 所对比的三位作者中,对现代社会为何显得如此恶劣甚至最恶劣不过的解释实际上也大相径庭。施密特认为人是「需要调和的」(sekundierungsbedürftig) ;他由此宣称人总是无法相互和平共处的危险本体。这也就是说施密特的理想其实是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再加上与之相联系的国内政治秩序,而自由社会和现代-浪漫主义的个体性则被他视为危险因素并加以拒斥。这种在规范性的理想与人类学的前提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三位作者笔下均颇为明显。福柯在早期文本之中将疯狂和死亡等僭越体验理想化,然而在他看来,现代社会已不再允许这样的体验。在此种悲观主义的视角中,人似乎成为了规训化和规范化 (Disziplinierungs- und Normalisierungstendenzen) 的滚滚潮流的受害者,人的自由发展在从不间断的文明进程中愈受掣肘。因此,人或者主体不应被设想为自主的本体,而应被设想为总是处于权力关系之中并且又不得不服从于权力关系。不过与此同时,福柯又相对乐观地认为,人就其被结构的性质而言本身就具有反抗的潜能 (Widerstandspotenziale) ;他在晚期的著作中则提倡以「存在的美学」和「对自我的关注」(›Sorge um Sich‹/« souci de soi ») 作为另一种可能的对于自我的关系。因此,人永远是可变的、实在的,永远不会被框定为某一确定的本体。福柯的人类学的结论则完全是双面的:一方面,作为主体的人是一种完全被权力渗透并受制于权力的本体。而另一方面,人在本体论上又悖谬地可以说是不确定的,总是有能力反抗的。相比之下,阿甘本寄希望于生命与形式之间的联结能够超越过去和如今所有已知的社会性的形式。和福柯一样,他希望摒弃对身份尤其是对人民 (Volk) 身份的描述,并且宣称弥赛亚的「余留者」(Rest) 的范畴实则是与人民身份相对立的。阿甘本同样反对通过「人类学机器」来创造人。就这种关系而言,与福柯一样,在阿甘本这里也有一种人类学——一种不愿被定义为人类学的人类学。阿甘本将人描述为一种由于人与动物的分离而在人自身之中产生的本体。如果说政治秩序是通过形式与生命的分离而构成的,那么人的存在就是通过上述的包容着的排斥而产生的,这种排斥反之将通过生命-形式即zoe与bios的调和所被摒弃。由此勾勒出的阿甘本的人类学也具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消极的人类学,它并不确定地描绘人,意即只描述人的否定的定义、它在文明的进程中被不断地划界与排斥的结果。然而,在第二个层面上,阿甘本的乐观主义观点则散发出这样一种信念:在原则上人可以寻得一种生命-形式,并明确地将人的存在与喜乐的承诺联系在一起。在这三个案例中,左右翼政治理论的分歧似乎最能在人的形象 (Menschenbild) 中找到依据,因为在施密特这里看不到对人的乐观的指涉,从而与福柯和阿甘本形成对比;福柯和阿甘本相对地在社会规范上与所谓的现代化进程的失败者和牺牲者站在一起,而施密特的理论则无法理解这种对他人的同情。正是通过重构衰落史、对时代的诊断、人类学和理想的对照方法之间的交互关系,我们能够进一步理解其所对应理论的构造和规范设置,并系统化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 
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 在三者那里分别勾勒出的历史哲学,则显示出同一种悲观主义的关联着的不同方面。施密特将政治建构为不可避的敌我划分——这与施密特「人是危险的」的人类学定义互为因果,并断言人与人之间共同的生活将始终充满冲突。政治继续潜藏着激化的可能性,因此「现实的敌意」升级为「绝对的敌意」的威胁也继续存在着。施密特认为政治能够在主权国家形式的体系中得到孕育,但他同时也对此进行诊断并预言了国家形式的消亡。他通过对于「守护者」(Katechon) 的表白而先验地超越了这种悲观的历史哲学。在施密特晚期的著作中才尤其得以勾勒出来的历史神学,以这样的意义解释了基督教的救赎史:「守护者」的使命正是要积极地阻止敌基督者。然而,施密特亦认为在20 世纪不再有任何力量堪当这一使命,因此在这一方面也就没有什么希望可言了。世界似乎陷入了永恒轮回的敌友划分的世界历史合法性之中,而这种组合总是意味着战争的阴云密布的「现实的可能性」。 和施密特一样,福柯也认为敌意和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理」。然而,直到70年代,福柯一直将战争描述为权力关系的运作逻辑,也就是说,即使是国家内部所谓的和平关系也总是被解释为一种内战式的冲突、有其战术和战略,并相应地总是以物理对抗的形式出现。因此,战争式的权力关系是历史运动的永恒法则,以此种方式运作的权力则自身就是有效力的;权力并非是由于或对于什么人才得以实现——权力本身就具有着或孕育着它自身的意义。相对地,应该注意到福柯在80年代则是将抵抗置于其权力分析的中心,致力于行动理论 (handlungstheoretische) 的论辩;尤其是福柯不再将权力作为一种战争关系,并藉此而含蓄地远离了先前的立场。尽管权力关系仍然不可避,并仍然在每一种可想象的社会形式中都有其体现,然而福柯现在的描述则更侧重于主体之间行使权力的相互关系:主体被清楚地、乐观地赋予了总是能够相对自由地自我决定的可能性。福柯明确地写道,在此之前,他只想处理问题而非解决问题。现在的(80年代的)福柯则是在肯定一种真正创造的、颠覆的、自主的自我关系的规范性之中寻求问题的真正解决。他因而不得不弱化权力并强化主体在他的世界建构中的意义,以便使他后期的建构与他总体的世界建构显得连贯。在福柯看来,权力不再构成性地奠基于强制、斗争、暴力和战争等等之上;不过这些方面仍可继续作为权力的部分或极点。因此,回到「福柯是否具有一种政治悲观主义」这个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一点,或许是福柯对于不再作为原则的战争式的权力模式的悄然修正。这再次表明,尽管福柯的悲观主义比施密特和阿甘本二者体现得更为明显,其实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间点的划分,也就是说取决于福柯的研究阶段和相应所讨论的文本。 
巴勃罗·毕加索 Massacre in Korea 和施密特和福柯一样,阿甘本考察了「世界范围的内战」,但他同时也在此之上强调了自古典时代以来的主权的分离逻辑 (Logik der souveränen Trennung) ,这种逻辑作为「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k) 而在历史哲学中占据一席之地。对于这种此世的 (diesseitiger) 悲观主义,阿甘本针锋相对地提出一种对于弥赛亚的盼望;弥赛亚的希望或应立即允许一种完全不同的时间体验,一种对于「纯粹的潜能」(reine Potenz) 的洞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弥赛亚主义并没有触及现存的主权和经济的必要条件。阿甘本所引介的退隐并不着眼于立即改变世界的结构——相反,它将继续存在,但在弥赛亚的退隐/出神 (Entrückung) 中,它只「无意义地运作」(gelten ohne Bedeutung) 。 基于这种种被建构起来的历史哲学叙事的背景,不同的未来似乎是可能的,由此产生了不同变体、不同程度的政治悲观主义。施密特担心政治会升级为「绝对的敌意」:在国家形式的时代结束后,任何此世的力量都无法阻止这一升级。福柯也认为未来的社会仍将由权力关系决定,但倘若我们采纳福柯晚期著作的观点,这些权力关系则并不一定以屈服关系 (von Herrschaftsverhältnissen) 的形式出现,也不可能对个体产生完全的影响。因此,随着福柯在70年代所做出的激进的评估逐渐褪去,「存在的美学」仍不失为一个机会:它允诺个体在一定限度内的自由。而按照阿甘本的表述,生命政治会继续造成更深刻的灾难,「经济的范式」亦继续推进人的无间异化。未来所剩下的无非只有退回到对生命-形式的、无关政治的弥赛亚体验。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施密特还是福柯和阿甘本都对于前现代的知识和神学领域有所涉足,并以期以这样的方式重获政治的行动力。施密特反思了被工具化了的神话,并希望自己的作品被理解为某种政治的神学。福柯则有时为「伊斯兰的政治灵性 (politische Spiritualität)」以及西方之外的情色艺术所着迷。换句话说,对于福柯,自由只能来自对于现代理性本身之根源的回应,因此他意图通过回到古典时代的实践来从现代的权力关系中解脱出来。阿甘本当然是寄希望于弥赛亚主义,并通过对于政治神学的解读将政治学和经济学都追溯到其神学的「起源」上。这些研究所具有的方式、程度和范围无疑都各有千秋,但同时亦都存在着一个显而易见的统一的要素:恢复并重新阐释前现代的知识体系,以便将它们作为现代政治的趁手工具。 因此,在三者这里都能够发现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之间的矛盾关系。在阿甘本的作品中是对于弥赛亚的乐观主义与对于此世的悲观主义直接地并存。施密特的并不承认神圣力量的信仰表白反对乐观主义,因为它先验地使此世的悲观主义变得愈发激进了。福柯的乐观主义则在晚期的著作中得到了极为明确的体现,而这些论述仅仅是在对早期著作中的阐释学式的片段进行修正的情况下,才能为福柯自己晚期的乐观主义提供依据。不出所料,施密特、福柯和阿甘本都并非绝对的悲观主义(这也就是说失败主义和虚无主义)者。无论如何,我还是试着指出这些理论中的悲观主义的面向,以及它们如何融贯于这些世界观的整体关系之中;以及,悲观主义的观点的确在这些著作中占据了颇为庞大的篇幅。因此,就施密特、福柯和阿甘本三者而言,显然没有人始终如一地持一种轮回式的悲观主义 (palingenetischer Pessimismus) 的态度。悲观主义的这一轮回变体,或许最可能出现在施密特的笔下。他对于国家社会主义的鼓吹并没有遵循旧世界终结、新世界随后重生的叙事,而是(暂时地)将由「领袖 (Führer) 」这一个体所代表的极权国家作为现代性孽生的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然而,无须赘言,施米特的这条「积极」的道路已经一劳永逸地被斩断了,随之而来的则是上文提到的对于遥遥无期的「守护者」的悲观主义解释。 
保罗·克利的画作《新天使》往往被阐释为一种轮回式的悲观主义历史观
最后,我的分析表明,施密特、福柯和阿甘本各自的世界建构都是表述性的。相对地,在我的分析中被应用的悲观主义态度在理想状态下所具有的三个典型特征——一般化、关于恐惧的美学和对自我的渲染 (Verallgemeinerung, Ästhetisierung des Schreckens und Selbstinszenierung) ——尽管这三个特征在三者的文本里都有所确证,但也可以看出其中明显的差异来。最值得注意的,莫过于施密特和阿甘本从不会公开批判他们自己这点:他们既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也不会修正先前的立场。在福柯那里,当然也有对自我的渲染,尽管其迹象略有不同。由于福柯并不那么执着于作为作者的身份,他得以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诚然,福柯并不总是清晰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从而使他的言语的建构特征在最后得以拥有一以贯之的主题,并且对于先前的工作多少有所自嘲。施密特和阿甘本在这里采取了不同的进路,他们一直是在以定言的方式提出他们的论点,从而筑牢了在其理论基础上描述的灾难将至的语境。 在这种情况下,认识论在施密特、福柯和阿甘本各自的著作中的意义与作用也就显而易见了。施密特以不同的方式为政治所带来的关乎生死存亡的威胁进行辩护,例如(所谓的)无关价值的经验论的、表述的方式,但也有基于人民 (von Völkern) 之本质的本体论的方式,在其他的情况下也涉及到对人类学不变量(「人是危险的」)的论述等等。由此,对于施密特来说,政治本身的相关性似从未受到过怀疑。而值得注意的是,施密特从来没有将政治自身的相关性显示为一项主题,就好像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几乎没有对施密特理论中知识的可能性产生什么影响。在施密特的理论建构里,偶然性只会作为政治决断的问题出现,而决断论又以秩序受到威胁为前提;因此决断似乎是一种足以摒弃偶然性并暂且减少施密特所预设的不确定性的途径。在这样的背景下,施密特指责了所谓「大众民主」(Massendemokratie) 的决策力的「丧失」(Verlust)。 福柯的文本则充满了对认识论的讨论,例如知识与权力相互之间的构成性的关系,或者主体可能获得的知识在可能性上的限制。然而福柯自己是如何反过来观察到这一点的,这一点还是没有完全得到解释清楚,尤其是福柯自己就作为一个在社会之中的主体,理应同样受制于结构的条件;而根据福柯的理论,哪怕是他自己也只能拥有受限的知识。不过福柯承认现代社会的偶然性和复杂性,尤其是在后来的论述中,他转而认为主体(在偏离的意义上的)另类可能性并非完全不可能的。这时,权力关系造成的限制也就不再如同早期的著作中所描述的如此密不透风。在福柯的建构中的规范性理想,则是以偶然性为其首要特征的、对于主体自身生命的复杂规划。 而阿甘本则寄希望于完全偶然的人类发展的可能性、寄希望于「纯粹的潜能」的体验。然而,他对时代的诊断并没有描述现代社会的偶然性而是其必然性 (Notwendigkeit) 。生命政治、主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等都被描述为是不可避免的,除此而别无其他可能。阿甘本所希望的「机器的空转」本可允许对主体化形式的摒弃,从而在复杂性和偶然性的意义上体验存在方式或者说「生命-形式」的「纯粹的潜能」。然而,就认识论而言,阿甘本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试图澄清他的理论构思所基于的观察立场。也就是说,阿甘本只在寥寥几处提到了在他理论之中知识在可能性上的限制 (Limitierung seiner Erkenntnismöglichkeiten) ,而且从来没有对他之前的论述进行过审视或提出过质疑。再加上阿甘本仅仅以范式来介入他的相对化 (Relativierung) 的尝试,这使他最终推断出任何「历史的起源」都无法得到确认;其中所包含的事实是,尽管阿甘本在每一本著作中都不懈地承诺要揭开「起源」的面纱,然而很明显,他并没有深入这个话题。 总之,这些悲观主义尤其是政治悲观主义的变体可以用以下的形式来概括:施密特代表了一种神学的悲观主义;福柯描述了一种乐观的悲观主义;阿甘本构建了一种弥赛亚式的悲观主义。对于三者而言。这样的分类法都各自揭示了自相矛盾的关系。施密特对历史的神学解释导致了一种悲观主义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世上似乎没有力量能够阻止末世的降临。这和施密特的建构又是矛盾的,因为救赎尤其不是问题,而只是「守护者」有所推迟。福柯关于历史是战争式的对立的论述在晚期著作中丢失了(或者说不再是讨论的主题了),取而代之的是通过个人的种种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得到阐述的乐观主义。阿甘本的悲观主义将当下描述为一场生物学意义上的灾难,并预言在现有条件下任何基于政治力量的反抗都将失败,但同时又许诺了一个弥赛亚式的当下。这种对时间和世界完全相反的看法,使一种生命-形式可以通过上文提及的激进的退隐被人真正把握。 无论如何,三者都各自显示出政治上的悲观主义特征。无论是施密特还是福柯和阿甘本都假定,在已知的政治解决的尝试中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合法性,而正是合法性导致了无效的解决方案以及这个恶劣的甚至最恶劣不过的世界。施密特的政治悲观主义把现在总结为一种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否认政治所带来的生存威胁,然而正是对政治的否认使得种种矛盾愈演愈烈,并将社会置于更为激烈地爆发的风险之中。导向极权国家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反而激起了彻底失控的战争狂潮。在这些事件之后,施密特认为没有任何国家的或者国际法的解决方案可以提供真正的补救,并预测全球的统一将会被过度的政治化所妨碍。 福柯将现代性描述为完全被规训和规范的技术所主导,而在其中主体则是他自己的可能性的条件。这一假设所依据的权力概念并不允许建立一个无权力结构的社会。与权力的斗争也会产生新的权力关系,而这种关系也有固化为权力关系的危险。现在,他的悲观主义的「多动主义」(Hyperaktivismus) 希望在任何看似可行的地方发起反抗。换句话说,福柯是在悲观地确信权力无法摆脱的同时,希望通过批判和抗议在可能的范围内找到创造更美好的世界的途径和时机。这为我们揭示了福柯理论之中乐观的面向以及其矛盾:一方面,福柯诚然诊断并预测了一种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的目标恰当地说来,不仅已经而且仍会继续失败。权力关系逐渐发展出了它自己的动力,使人无法通过主体自身的或是集体的行动来把握这种动力 (是的,甚至根本没法把握) ,因此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无法确保一条出路。另一方面,福柯试图找到摆脱这种政治悲观主义的方案,尤其是他晚期的那些著作,但这些方案无不是对于个体而构建起来的自我关系:福柯试图通过回归古希腊-罗马的传统形式来构想新的自我关系,从而将主体抽离出社会的集体组织的领域。这背后是一种乐观的信念:如果每个人都如此行事,那么所有人都会有更多自由。在这种关系里,福柯只是粗略地探讨了政治行动可能出现的意外、因行使自由而对他人自由造成的限制,以及权力的战术和战略 (Taktiken und Strategien) 。他似乎假定,只要每个人都关注好自己,那么很多问题总是会迎刃而解的。最后,阿甘本完全放弃了改革(改良)或者革命(反抗)的任何希望。根据阿甘本的政治悲观主义,在现有条件下,世上不可能再有什么解决方案。无论是民主还是其他所有形式的政治组织似乎都不再奏效。阿甘本的未来政治学所寻求的出路乃是与世界建立一种不同的关系,这种关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的关系,因为(与福柯类似)它不再相信有任何能够约束人的决断、博弈的过程或者对于世界的集体的塑造,而是退回到对时间的另一种感知中。最终,在「弥赛亚时间」中,任何在世界内部改变世界的主张都会被彻底抛弃。 总之还是应该指出,尽管我在分析中对这三种理论给出了批判性的讨论,但我其实不想给人一种印象,以为我是在以「对进步的虔信」的名义,以及/或者以「客观科学」的名义提供相反的论据。我的目的也不是要找出三者那儿有可能会应验的诊断。现代社会现在是否「真正」由生命政治、规训或政治决断力的丧失所决定,以及这是否就证明悲观或乐观的预期是合理的;对于这些,我都既不能也不想从我所选择的建构主义的观察者的视角来判断。在赞同和反对这两极之外,本文只是旨在通过悲观主义理论及其意义并在其中(重新)建构现实。研究表明,三者都有通过语言(也就是说,他们各自的作品)来创造出各自的世界建构,这种世界建构在贯穿他们写作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既有一部分发生了变化,也无疑有一部分保持不变。从三者理论的角度来看,当下似乎弊端重重,而现有的政治解决方案则也是不充分的甚至破坏性的。施密特、福柯和阿甘本各自发展了一种批判理论,这种理论首先创造了它所要批判的内容,然后从这一观点出发来考虑政治上的替代方案。在这之中,施密特、福柯和阿甘本所看到的(或者说根据我所重新建构的)政治行动的限制以及(不)可能性逐渐显现出来,这也是由这些理论所持的立场相应的逻辑来衡量的。政治悲观主义就体现在诊断和治疗方案的交互关系中。 最后,对于本文所选择的研究设计还应该指出的是,这项政治学研究也是对人文社科理论的反思:本文的理论性和比较性的理论取向要求一以贯之地在社会学、哲学、文学和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的接口上。这种跨学科的立场和相应的方法,一方面可以用悲观主义的主题来解释,因为悲观主义无论在哪个学科之中都具有历史的和当下的意义。另一方面则是要归功于三位哲学家,他们都并非政治学家,而是本身就处在不同学科之间与之中。就我所讨论的主题群而言,其研究的成果也来自各学科的广泛的领域,在其中政治学并没有占主导地位。在此,十分明显的是,学科之间的界限实则比我们所想的要透明地多。譬如当下对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理论的许多贡献并非是来自政治学家,这一点就很能说明问题。因此,我的研究所具有的与政治学的相关性,主要还是在于悲观主义与其政治后果之间的联系:在对世界的认识与在对世界种种可能变化的认识之间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和交织,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我在本文中并没有对后者的可能性做出过什么表述。我的研究可能由于这种取向,或是由于建构主义的前提以及相关的意识形态禁忌而令一部分人感到不快。然而与此同时,本文的价值或许恰恰就在于它的克制,它有意地、明智地避开了道德的以及/或者鼓动的政治说教。相反,我的研究方法展现了社会性是如何通过观察而被建构的,并藉此而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现代性的观察者,施密特、福柯和阿甘本,以及他们的观察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或许都没有认识到他们的观察在可能性上的局限,并假定他们所说的是独一无二的「真知灼见」——这种见解也影响着作为社会之中的社会科学 (Politikwissenschaft als Wissenschaft der Gesellschaft in der Gesellschaft) 的政治学。 这三种理论是否「真正」代表了某种政治悲观主义,这实则是也总会是一个关乎视角的问题,而本文所采用的视角旨在提请读者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不是因为它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时刻流变,而是因为它总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观察。这种视角的转变或其可能性不仅是社会科学理论的一个特性,而且在其他情况下也是可能的,有时甚至是可取的。/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Philosophia 哲学社
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备战深国交网”除发布相关深国交原创文章内容外,致力于分享国际生优秀学习干货文章。如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原谅,并联系微信547840900(备战深国交)进行处理。另外,备考深国交,了解深国交及计划参与深国交项目合作均可添加QQ/微信:547840900(加好友时请标明身份否则极有可能加不上),转载请保留出处和链接!
非常欢迎品牌的推广以及战略合作,请将您的合作方案发邮件至v@scieok.cn本文链接:http://www.scieok.cn/post/4524.html
-
<< 上一篇 下一篇 >>
施密特、福柯和阿甘本的政治悲观主义 / 翻译
36495 人参与 2024年02月05日 14:58 分类 : 深国交哲学社 评论
search zhannei
深国交2024年英美本科录取小计
-

未标注”原创“的文章均转载自于网络上公开信息,原创不易,转载请标明出处
深国交备考 |
如何备考深国交 |
深国交考试 |
深国交培训机构 |
备战深国交 |
联系方式
Copyright www.ScieOk.cn Some Rights Reserved.网站备案号:京ICP备19023092号-1商务合作
友情链接:X-Rights.org |中国校园反性骚扰组织 | 留学百词斩 | 南非好望角芦荟胶 | 云南教师招聘考试网 | 备战韦尔斯利网| 备战Welles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