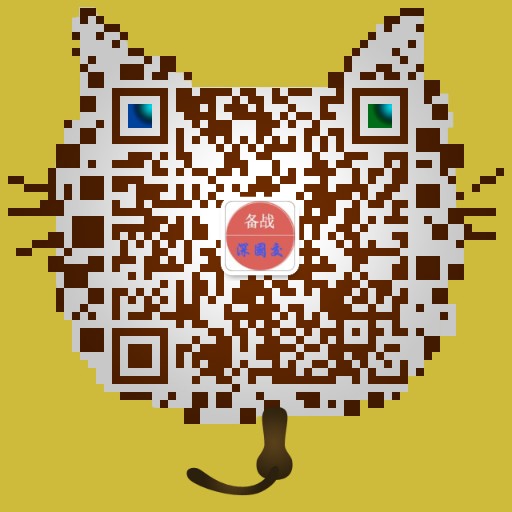当前位置:首页 » 深国交哲学社 » 正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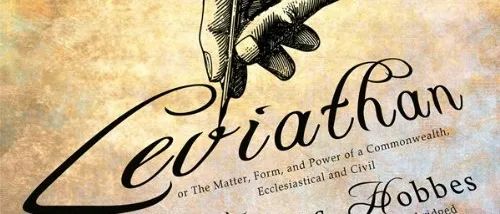
(接上文) 
解释 一个为霍布斯式的叛乱权辩护的可能的思路是,霍布斯会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订出足够的法规来规定人们的一切言论和行为,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办到的;这样就必然会得出一个结论说:在法律未加规定的一切行为中,人们有自由去做自己的理性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事情」(Leviathan Ch.21),即,在法律的沉默处(silence of law)即有自由。然而法律没有规定臣民没有叛乱权——或者即使规定了也是无效的——因为「实定法本身不被反对」的规范性之有效性不能来自于实定法自身,即,你要先接受实证法,才会接受实证法要求你不反对它;而如果你选择不接受实证法,实证法则没办法要求你不反对它。 这种辩护思路将会是失败的,因为霍布斯明确提到了主权者应该将「禁止叛乱」划入实定法。不过实定法的规范性基础的确是自然法与主权者的教育,而非实定法本身[0]。然而,一方面霍布斯所说的,是「法律的沉默处」,而非「法律的失效处」;另一方面,霍布斯会认为,如果主权者试图给予臣民某种可能使得建国契约的意图落空的自由或权利,这一给予就是无效的。 还有一种可能的辩护思路,是通过个人抵抗权的集合构成叛乱权。如Hampton的著名解释,由于霍布斯为个体留下了抵抗权,那么个人就拥有不服从君主的个别命令的权利。这就意味着,人民被允许作为一个整体、拥有集体权利,当他们认为这个君主不利于他们的自我保全,或他人做统治者更好时,就撤回他们对于该特定主权者的效忠。很明显,这和霍布斯的其它说法矛盾,比如「『每一个平民都是善恶行为的判断者。』这说法在没有国法的单纯自然状况下是正确的,同时在民约政府之下在没有法律规定的事情上也是如此。但在其他情形下,善恶行为的尺度则显然是国法,而法官则是立法者——他始终是代表国家的。根据这种错误的理论,人们会在心里打算盘,对国家命令持异议,然后按照个人判断,看看是否合适再来决定是否服从,这样就会使国家陷于混乱并被削弱。」(Ch.29)进而,Hampton认为,霍布斯的建国方案失败了[1]。 运用上述「理性」概念的区分,我们将发现,Hampton的可能错误在于,虽然霍布斯认为有些行为无论如何都不能被理性判定为「有利于自我保全」,但自然状态下无人事实上能判定这一点,而只要人们声称自己是理性的,那么现实地,我们不能说「谁对什么没有权利[2]」。由此,在自然状态下,人们的大多数私人判断都被赋予了权利;接着,理性推算的结果是:我们应该进入国家并上交私人判断权。尽管个体被赋予了在「当一个人受到攻击、害怕立即丧生时,如果他除开击伤攻击他的人以外,便找不出怎样躲避的方法」的时刻,不管对方是否是主权者或其委派人员,都能恢复私人判断权[3]并进行抵抗的权利;但,是否因为每一个不同的个体都有权进行个体抵抗,就有权利联合起来更换主权者或进行叛乱,是有待理性重新评估的。「抵抗权」成立的原因在于,这与契约的目的违背(「这种义务便不决定于我们表示服从的言辞,而只决定于意向,这种意向则要根据所作事情的目的来加以理解。因此,当我们拒绝服从就会使建立主权的目的无法达到时,我们便没有自由拒绝,否则就有自由拒绝。」)(Leviathan,Ch.21),而个人抵抗不会使个人保全更加受损;但「抵抗权」的联合是否依然成立、发动「叛乱」是否能有利于主体,是需要再次评估的[4],即,抵抗权不能直接相加成为叛乱权。 一种抗拒叛乱权的思路如下:Joseph Raz在他的解释中区分了一阶理由和二阶理由[5],一阶理由是比较诸利害,二阶理由是不顾利害而做/不做。在Joseph Raz式的解释者看来,主权者的权威/对主权者的服从是二阶理由,即当臣民遵从主权者时,他是不顾利害的(就好比,当我们去救我们落水的孩子,对落水的孩子的关心构成了二阶理由,此时我们是不顾利害的);而Hampton的错误在于,由于这种对主权者的服从是二阶的,个体没有行为功利主义式的判断权,不是通过利害计算才服从主权者的。 这一区分类似于上述对「双层利己主义」的讨论。尤其当我们进入国家之后,理性推理的结果是:在实践推理中,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仅可以盲从自然法,还可以盲从实定法。如Hart所说,这可以很好地刻画霍布斯的理论[6];但是我们会反对将「自我保全」归为一阶理由,而认为如果采用这种区分,就必须把「自我保全」归为二阶理由,抵抗权则是二阶理由之间的争端,否则无法解释在「有权抵抗」的案例中为什么一阶的理由为什么能够阻止二阶理由。然而,这种理论并没有在避免叛乱权上做得更好,因为在二阶理由中有对主权者的服从、有自我保全,甚至有父母的保全,这种二阶分类却无法解释二阶理由的边界(如:为什么不能有「共和主义式的自由」?)及二阶理由之间的排序。 换而言之,既然在理性容许的一些情况下(如杀害父母、残害自己、杀害主权者本人),我有权不听主权者的命令,甚至当主权者威逼我时,我有权进行抵抗;那么,为什么我在「维护共和主义自由」这件事上无权不听主权者的,并在受其威胁之时无权抵抗?二阶分类看起来无法回应这个问题。 Susanne Sreedhar为叛乱权辩护的方案更复杂。为了解释上述的一些矛盾,她提出,虽然霍布斯没有明确的表达,但实际上他按照以下三条标准判定一个契约的有效性或「权利」的授予与否: 1)合理期望原则:要求有效契约的当事人能够合理地期望对方履行契约; 2)忠实原则:禁止权利在与签订盟约的目的相抵触的情况下在盟约中转让; 3)必要性原则:将契约中转移的权利限制为契约实现其目的所必需的权利。 并且,「避免死亡或自残」仅在建国契约中是不可让渡的权利,而并非在所有契约当中,因为完全可以有其它的「民间契约」,选择死亡来避免更大的恶。Susanne认为,之所以死亡不是最大的恶,是因为霍布斯认为死亡仅仅是最大的自然之恶,但在自然之恶外还有社会之恶;所以,在社会中养成的某种新人性完全有可能会把一些事物识别为更恶的。比如士兵合同,因为并非建国契约,所以可以牺牲生命;完全可以有个别社会人认为追求荣誉比避免死亡更可欲,或者认为提高自已的牺牲概率来保卫大多数人的自我保全的概率更可欲;或者在保护父母的案例里同理。这是在个体层面解释权利的归属问题。 可能会有人批评,为什么不简单地将这些以死亡为可能后果的契约归为不理性的,或者,甚至将所有可能相关的契约都归为无效契约?Susanne Sreedhar的回应大体如下:霍布斯在《论人》、《论公民》等各处都承认有自杀的案例,所以自杀在心理学上不是不可能的;同时,霍布斯承认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导致死亡的行为的权利存在,而权利是一个理性概念,所以可能导致死亡的行为不一定是非理性的。 
Susanne Sreedhar / 图源:Boston University 然而,当代解释者经常面临的困难,正是他们对霍布斯的解释结果时常是霍布斯本人没有明确表达过的。霍布斯谈到「避免暴死作为不可让渡的权利」等原则时并未特指建国契约,而是泛指一切契约。Susanne Sreedhar自己也发现了这一点,但她只能将其归之为霍布斯论述的缺陷。 在集体层面上,要想从抵抗权论证叛乱权,会面临三种挑战:非主权者的联盟的形成的不可能(Susanne称为「形而上学的不可能」)、契约合同的不可能和审慎理性的不可能。 非主权者的联盟的形成的不可能,即「一个非利维坦式的联盟是可能形成的吗?」 霍布斯会认为:「一群人经本群中每一个人个别地同意、由一个人代表时,就成了单一人格;因为这人格之所以成为单一,是由于代表者的统一性而不是被代表者的统一性。承当这一人格而且是唯一人格的是代表者,在一群人中,统一性没法作其他理解。因为一群人天然地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Leviathan Ch.16)「但对整个人群,即作为有别于个人的人格而言,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恰当地说这是我的而不是别人的,也没有什么行动应当归属于这个人群,被看作他们的行动。[即使他们全体或其中部分人达成了一致,]他们所进行的并不是一种行动,而是就像有许多个人一样有许多种的行动。」(De Cive,6.1) 也就是说,「人民的叛乱」是一种语词或形而上学错误。看起来霍布斯不认为利维坦之中个体与个体之间能合法地组成成一个统一体。Susanne Sreedhar对此的回应是,只需承认个人拥有的参与集体行动的权利(这是霍布斯承认的,即Leviathan Ch.21"自由联合起来互相协助、互相防卫"),而非集体行动本身的权利;但是这一解决方案明显是有问题的——这一个体权利的实现,需要以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为前提,如果集体不可能,这一权利就是空中楼阁。 但是在De Cive中,霍布斯事实上承认发生集体叛乱是可能的,只是不能称之为「人民」或「一个统一体」的行动,而只是达成一致的「许多个人的许多种的行动」。这样看起来就不是一个很强的危险——只要现实地、可以发生叛乱就够了,形而上学上或者语词上怎么称呼看起来不太重要[7]。 另一个可能的回应思路是,可以再找一个法人(person),再建一个利维坦;比如霍布斯也暗示,对叛乱者的敌对行为,就类似两个国家的斗争[8]。同时,一个非利维坦式的组织方式也是可能的,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联盟」。「因为联盟是人们根据信约联合而成的,如果象单纯的自然状况一样不将权力交给任便一个人或会议来强制履行信约,那么联盟就只有在没有出现正当的互不信任的理由时才是有效的。」(Leviathan Ch.22) 联盟可能更易瓦解,但是有鉴于叛乱者比自然状态的人,完全有可能更有理性(因为经受过教育),我们可以认为存在这样的可能性:①主权者把一群人处以死刑,或者告知他们,如果他们不杀了自己的爱人/亲人,主权者就杀了他们,并且没有宽赦;②这个国家里的大多数人都是「疯子」(在霍布斯的意义上),或都是上文提到的那种冷静而具有奇特的身体结构的人。他们经过反思平衡而成为了马列主义者,认为共产主义信仰是他们个体生命中最重要的「善」。那么,他们可以建立起一个非利维坦式的联盟,(即使可能会瓦解,但也)足以让他们开始叛乱,直到成功,或蜕变成为另一个利维坦,或被消灭。 至少「非主权者的联盟的形成的不可能」不能排除这两种可能。 在进入「契约合同的不可能」的讨论前,我们首先需要澄清:叛乱者还是臣民吗?这一点之所以需要澄清是因为,如果叛乱者不是臣民,如S.A. Lloyd或者Peter J. Steinberger或者Michael Davis[9]所认为的那样,「契约合同的不可能性」的论证难度就降低了:论证目标从「存在某种情况,可能不为不义地在建国契约之下,作为臣民叛乱」转为「存在某种情况,可能不为不义地退出契约」,从而不用在乎契约里的叛乱是否正义。 在Leviathan中,霍布斯将「臣民」的标准刻画为「臣民对于主权者的义务应理解为只存在于主权者能用以保卫他们的权力持续存在的时期。因为在没有其他人能保卫自己时,人们的天赋自卫权力是不能根据信约放弃的。」(Leviathan,Ch.21)但是这一标准看上去并不清晰——什么是「用以保卫他们的权力持续存在」?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案例来进行研究。比如:叛乱者(开始叛乱是不义的,但是已经叛乱而互相帮助、继续叛乱则不为不义)、被蒙赦的叛乱者(被蒙赦之后继续叛乱主权者是不义的)[10]、被敌人抓走的士兵(旧的建国契约失效,可以签新的服从契约)[11]、被绑起来的奴隶(不能签新的契约,被释放后才能)[12]、受于恐惧的奴隶(可以签新的契约)与被敌军抓走的主权者(建国契约依然有效,要听从主权者授权的那些大臣)[13]。 
英国内战的战俘 / 图源:oxford Ashmolean Museum 前两个案例无法澄清臣民标准:叛乱主权者这一行为的正义程度,不能用来判断叛乱者是否还算臣民。通过后几个案例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建国契约有效性的边界是主权者依然有权力(不一定亲自行使),这一权力尚在保护我们,且我是在行动自由的情况下签订契约的;在这个边界之内,我才是臣民。根据这个标准,我们有理由认为叛乱者不再是臣民,因为主权者虽然有权力,但是这权力不再保护我(当然,主权者完全有可能制定了一个保护叛乱者免受非国家军队之外的伤害的法律,那么叛乱者就是臣民)。 同样,在讨论惩罚权时,霍布斯倾向于认为叛乱者并非臣民。「施加于国家代表者身上的损害不是惩罚而是敌对行为。……对于公敌所施加的损害不属于惩罚范围……法律所规定的惩罚是对臣民的惩罚,而不是对这种曾经以自己的行为充当臣民又明知故犯地叛变、否认主权的敌人的惩罚……对于臣民中那些蓄意否认本国已建立起来的主权的人说来……犯这种罪的人便不是作为臣民、而是作为敌人遭受损害的。」(Leviathan,Ch.28)但是在一些地方,霍布斯依然使用了「叛乱的臣民(rebellious subjects)」这一称呼,如Leviathan Ch.40,而他本人明确反对错误的语词用法。总之,虽然根本上叛乱者是否是臣民依赖于主权者具体的法律,但是大部分证据倾向于反对Susanne Sreedhar,即叛乱者不再是臣民。 进而,我们要面对「契约合同的不可能」的挑战。 霍布斯在De Cive中认为,要想合法地推翻一个主权国家,就①必须得到这个国家所有成员的同意,不能直接进行多数决议;②在得到同意的场合,需要掌握着主权的人或议事会召集公民,同意他们推举一些人出来接受代表推举者发言的权威;③主权者决定,在他所提交讨论的议案上,多数代言人的意见可以代表全体代言人的意见。但有鉴于并非所有人都同意,主权者也不会为讨论他自己的权利而召集起公民,除非他出于极端的厌恶而用明确的方式放弃了权力,所以不可能合法地推翻一个主权国家(De Cive 6.20)。而在Leviathan中,霍布斯认为①反对主权者就是反对自己;②个体臣民的权利已经交给了代表者,臣民之间不能再正当地奠定契约。 (在Susanne Sreedhar认为叛乱者依然是臣民的前提下,)她的解决方案是抵抗权不能过渡给主权者,所以契约之后,授权和抵抗权的保留是融贯的。我们可以不采取授权中的规则来叛乱,而采取抵抗权的联盟的方式。这类似于Hampton的思路,但仍受到上文的挑战:权利这种道德地位的联合不见得能生成权利,因为可能通过不了理性的评估。此外,还需指出霍布斯的一处不融贯:在Leviathan中,霍布斯认为,选出主权者需要采取多数人决议的方式(Leviathan Ch.18);那么为什么在De Cive中,霍布斯会认为废除或更换主权者就必须全票通过?一个可能的回应是两者的过程不一致:Leviathan是一些人先普遍同意建国(Ibid.)再向外推广,若不接受多数人已选出的主权者就会被杀死,不审慎。但是这一理由是不足的:在废除主权者的事情上,不听极权统治者的人也会被杀。 此外Leviathan还在有些段落中声称,反对主权者就是反对自己。这一表述很模糊,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反对契约中授权给主权者的行为就是反对自己。反对主权者杀我的行为不是反对我自己,反对「当我触犯法律,主权者可以来杀我」才是反对我自己。 第三种挑战是审慎理性的不可能,即霍布斯认为,叛乱不可能通过理性的评估[14]。 在这里,霍布斯对叛乱权提出的挑战是:无论如何,发动一场叛乱都不可能符合叛乱者的理性,即,经过反思平衡,不可能被叛乱者认为是「善好的」。他给出的理由包括:「第一,不管一个人对任何事情能怎样地预计到并能有多大的把握性,当他去做一件足以导致他自身毁灭的事情时,那么不论会有什么他所不能预计的偶然事物出现使之有利于他,这种情况都不能使他做上述事情成为合理的或明智的。其次……任何人要是没有联盟的帮助便都难望依靠自己的力量或智慧防卫本身,免于毁灭之祸……要是有一个人宣称他认为欺骗那些帮助他的人们是合理的行为,那么,他有理由能够期待的保障安全的手段便只是从他一个人单独的力量中所能获得的手段。因此,破坏信约之后又宣称自己认为这样做合理的人,便不可能有任何结群谋求和平与自保的社会会接纳他,除非是接纳他的人看错了人。当他被接纳并被收留时,他也不可能不看到错误中所蕴藏着的危机;因为按理说来,一个人不能指靠别人的错误作为保障自身安全的手段。因此,如果他被遗弃或驱逐出这一社会时,他就会毁灭;而他要是在这社会中生活下去,则只是由于别人的错误;但别人的错误他是既不能预见,也不能指靠的,因之便是违反他自我保全的理性的。这样看来,既然说大家都没有促使他遭到毁灭,那么这种情形便只是由于没有弄明白怎样于自己有利才把他容忍下来了。」(Leviathan,ch.15)叛乱者的成功是极其偶然的,理性对于自身保全的要求不能依赖于偶然性;并且,叛乱者将被「结群谋求和平与自保的社会」所抛弃。 「但人们在这一点上也许会提出反对说:臣民的景况太可怜了,他们只能听任具有无限权力的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的贪欲及其他不正常激情摆布……其实一切政府形式中的权力,只要完整到足以保障臣民,便全都是一样的。人类的事情决不可能没有一点毛病,而任何政府形式可能对全体人民普遍发生的最大不利跟伴随内战而来的惨状和可怕的灾难相比起来或者跟那种无人统治,没有服从法律与强制力量以约束其人民的掠夺与复仇之手的紊乱状态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应当看到最高统治者的最大压力决不是由于自己高兴损害或削弱臣民或者是由于象这样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才施加的,他们自己的力量和光荣存在于臣民的活力之中。这种压力来自人民本身的抗拒情绪,他们为自己的防卫而纳税是很不情愿的。这样就使得统治者不得不在平时尽量从他们身上征敛,以便在任何紧急时期或突然有需要的时候御敌制胜。因为所有的人都天生具有一个高倍放大镜,这就是他们的激情和自我珍惜;通过这一放大镜来看,缴付任何一点点小款项都显得是一种大的牢骚根源。但他们却不具有一种望远镜(那就是伦理学和政治学),从远方来看看笼罩在他们头上,不靠这些捐税就无法避免的灾祸。」(Leviathan,Ch.18)如果主体进行长期评估就会发现,国家存在无论如何都会比没有国家存在更符合自己的善好,或,发动叛乱的后果无论如何都不符合自己的善好;共和主义分子都是被古代书籍蒙骗而对后果产生认知错误的人[15]。 
18世纪英国收税情形/ 图源:大英博物馆 「至于以叛乱取得主权的另一例子则可以显然看出:虽然可以得到这种结局,但由于按照常理无法预期,而只能预计出现与之相反的情形;同时,像这样获得国权以后,其他的人就会起而效尤,所以这种举动便是违反理性的……有些人……认为破坏信约有助于获得永恒至福,因而便是合乎正义和理性的。这种人就是那些把杀戮、废黜或反抗经过自己同意建立起来管辖自己的主权者认为是一种功德的人。但我们对于人们死后的状况并不具有任何根据自然之理得来的知识,更谈不到那时对失信会给予什么报偿的知识,这种信念所根据的不过是听到人家说他们以超自然的方式知道了这一点;或者是说他们知道有人了解到别人知道旁人以超自然的方式知道了这一点。」(Leviathan,Ch.15)类似于孟子所谓「上下交征利」的情况,叛乱的成功与否本就是无法预期的,即使成功,也会招致新的叛乱;认为今世的叛乱可以带来永恒的至福,则是没有理由的盲信。 此处霍布斯的论证看起来有些弱,且与其它部分的论证相独立。为凸显这一论证的缺陷,我们只需考虑这样一个案例:如果一个主权者,很好地履行了「主权者的职责」中对臣民「教育」的责任,「了解他这些基本权利的根据与理由……教导人民认识这些根本权利(即自然的基本性法律)……防止叛乱对他的自然人身所带来的危险」(Leviathan Ch.30),「以使大家不会相信每个人随心所欲地去生活比组成一个国家更好」(De Cive 10.1),而让臣民认为「没有这种独断的政府,这种战争就会永远持续下去」;与此同时,这个主权者在其它方面肆无忌惮、酒池肉林、鱼肉百姓、独夫民贼,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什么都不会发生。因为他的臣民足够理性,(依照霍布斯)意识到即使这个主权者很糟糕,叛乱或主权者只会带来更糟糕的局面,所以只能默默忍受。你愿意接受这样的后果吗[16]? 或者为了凸显这一论证的缺陷,我们回到一个实际的案例。由于建国契约的签订双方不是主权者和臣民,主权者对臣民没有义务,但依然需要遵守自然法;即主权者有其职责,而这一职责朝向的对象则是作为「主权者的主权者」(Cf. Leviathan Ch.33)、「自然法的作者」(Cf. Leviathan Ch.42)的上帝。上帝如何对主权者进行规范?通过「自然惩罚」,即事实的规范性。「在这个(后果之)链中,苦事与乐事连接在一起,其方式使想要作出任何纵乐行为的人必将遭受与之相连的一切痛苦。这些痛苦就是这些行为的自然惩罚,而这些行为则是害多于利的景况的开端……不义招致仇敌的暴行之罚、骄傲招致失败之罚、懦弱招致压迫之罚、王国疏于执政招致叛乱之罚……自然的惩罚……由于破坏自然法而来。」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不对称的关系,即当主权者疏于执政而引发了叛乱,「主权者被叛乱」就是符合上帝意图的、来自自然法的惩罚;但是叛乱者进行叛乱,则是违背了上帝意愿和自然法的、不合理且没有权利的行为。换言之,按照霍布斯的理论,存在某一事件A(X2对X1施加某种行动)中,其行动主体X1遭受X2的行动是契合上帝意愿的,行动主体X2做出这一行动却是违背上帝意愿的。在这里,上帝的意图真的变得不可揣测了。 霍布斯可能会怎样回应这里的挑战呢?他会说:「是否对于暴君也应该事事主动服从?或者说,一个合法国王的所有命令都该被服从?如果在我父亲被法律判处死刑的情况下,他命令我用自己的双手去杀死我的父亲,那该怎么办?……没有必要考虑这一情况。我们从未读到也从未听说过有哪个国王或暴君这样没有人性,发出这种命令。如果有谁这么做的话,我们要考虑那一命令是否是他的一项法律。因为我们说的不服从国王的意思是不服从他的法律,也就是那些在其被应用于任何具体的人之前所制定的法律……如果你所说的命令被写进了一般法(这从未发生过,今后也绝不会发生),那你就必须服从它,除非你在法律颁布之后以及你父亲被定罪之前离开这个国家。」(Cf. Behemoth Part One)他会说:「如果说一个不信基督的国王,明知道自己有一个臣民期待着将来基督在现今的世界被焚烧后第二次降临,并打算到那时服从基督(这就是相信耶稣是基督的宗旨),在目前则认为自己有义务服从他这位不信基督的国王的法律(这是所有的基督徒在良心中都有义务要服从的)而他又把这臣民处死或对他进行迫害,试问世界上有这种不近人情的国王吗?」(Cf. Leivathan Ch.43)他会说:「他们认为,这个至上者会对人进行逮捕、剥夺和杀害,而人人都相信也许下次就会轮到自己的。但至上者为什么会这样去做呢?……他不这样做才是符合正义的,也即不会违背自然法和对上帝背信。因此,一个君主的誓言为他的臣民提供了某种安全……即使他这样做是符合正义的,即使他无视他的誓言,那他也没有理由去作践他的公民。因为这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处……政体本身的有利和不利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同样的,是两者所共享的。」(De Cive 6注释三、9.2) 也就是说,有鉴于主权者利益与臣民/国家利益的统一,霍布斯认为,不会有暴君的。(不过即使在某个平行世界有,你也要服从其法律。)或许诚如Watkins所说,「霍布斯只经历了内战这一场灾难,而我们却经历了内战和集权主义两场灾难。[17]」这些在霍布斯看来不太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也可以被接受的理论后果,在我们看来则成为了时时警惕的灾难。 
结论 既然Jean Hampton、Susanne Sreedhar等解释者的阐述与霍布斯本人的论证都多多少少有点问题;而霍布斯要想融贯,其权利理论必须成为一个如上所述的理性推理的结果,那么这种理性会允许叛乱吗?简单地将其归为「霍布斯发起的叛乱」或者「这种理性拥有者发起的叛乱」是不够的,因为霍布斯可以回应说,正确的哲学家也没有发动叛乱的权利。「因纵使是教导正确哲学的人有不服从的情形时,也可以合法地加以惩罚[18]。」(Leviathan, Ch.46)因为,这一理性会认为这种无政府的伦理学是一种错误的伦理学,比如亚里士多德式的伦理学;而我们看起来必须接受「任何政府形式可能对全体人民普遍发生的最大不利,跟伴随内战而来的惨状和可怕的灾难相比起来,或者跟那种无人统治,没有服从法律与强制力量以约束其人民的掠夺与复仇之手的紊乱状态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的情形。 然而,回到自然法的最根本处,一种叛乱权依然可以克服霍布斯的推论,并通过霍布斯式的理性被保有。在具体论证中,霍布斯从未拒绝将「两恶相比选较小」视作理性思考的可能情况。「不反抗的义务是在现在的两种恶(反抗而死和不反抗而死)之间选择较大的恶的义务。无论怎样的死都是比反抗更大的恶,但是,不在这两种恶之间选择较小的恶又是不可能的。因此,就不反抗的协议而言,是在对不可能的事负有义务。」(De Cive 2.18)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在理性中引入量的比较,不论是概率的还是程度的;那么,如果集体叛乱能带来超过其恶的善好(比如上文既是出色的教育家也是糟糕的暴君主权者的案例),为了我们的生活、家人的生活、后代的生活、我们的尊严与行动的自由(这些都被霍布斯视作广义的自我保全或好的生活所要求的),一些极端的集体叛乱总是能被赋予权利。霍布斯可能会反驳说,一旦开「只要符合某种条件,叛乱权就是可能的」之先河,霍布斯式的人就会无休止地、自以为理性地认为自己符合这个条件,那些富人、贫穷而顽强的人和倨傲的人就会不停息的发动叛乱。霍布斯式的人看上去确有这个危险,但若霍布斯本人真诚地这么认为,那么由于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很多叛乱,包括护国公克伦威尔或英国皇室复辟的叛乱,他们都宣称自己拥有正当性,那么任何一个国家看上去都是会被推翻的。宿命已定,还挣扎什么呢?难道我们要克伦威尔或英国皇室宣称自己的革命或复辟是违背上帝意志的吗? 
奥利弗·克伦威尔 霍布斯同样会说:「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共和国能未经历改变或叛乱而长久维系……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哪个最伟大的共和国能够长时间地免于叛乱。……如果民众在每场叛乱一开始就知道这项原则,一旦政府建立起来,那些野心勃勃的人就绝不会有希望扰乱他们的政府。因为没有人帮忙,野心什么也做不了,而如果普通民众都接受了关于他们义务的正确原则的谆谆教导,也就几乎不会有人助长叛乱……B:就我所观察到的来说,只要这个世界延续下去,所有的基督教国家都将遭受这种阵发性的叛乱。A:很有可能。然而,正像我已经说过的,这类错误通过改进大学很容易得到矫正。」(Behemoth Part 2)即,尽管叛乱必将发生,而没有哪个国家能避免,原则上只要通过教育,错误是可被纠正的。「只要符合某种条件,叛乱权就是可能的」这道口子不会引发无休止的叛乱——我们不是还有隐微学说、内传学说吗? 这一论证还可以以另一种形式进行。霍布斯经历了1653年克伦威尔就任「护国公」、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再之前,英国还经历了罗马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古萨克逊人、法国人等的入侵(霍布斯在DPS中特意提及了这几段历史)。只要霍布斯认为,现在查理二世治下的英国比罗马人时代的英国更好,或者更宽泛地说「通过历史上无数叛乱而建立起的现代国家比叛乱发生前的小国家更好」(比如「生活在现代中国比生活在夏朝更好」),而这一变化不可避免地需要叛乱作为途径,霍布斯就必须认为这些叛乱是被理性赋予「权利」这一道德地位的;即反思性地评估,总有一些叛乱带来的政治上的整体对自我保全的好处,是超过一段时间的不和平带来的自我保全的损害的。有鉴于霍布斯回应抱怨本国君主的言论,「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在征服者时代过着怎样的生活,那时候身为英国人是一种耻辱,如果他对诺曼主人安排的低下职位噪喽抱怨,得到的没有别的回答,只会是『你不过是个英国人嘛』」 (DPS,Of Sovereign Power)我们有理由相信,霍布斯真诚地认为生活在查理二世治下比生活在征服者威廉一世治下更好;尽管这需要以一些叛乱为代价,但如果不付出代价,他将永远作为低等人生活。如果这些叛乱是不可避免地通向更好的情况的途径,那么,这些叛乱就必须被理性赋予权利[19]。/ 注释与参考文献:(滑动查看更多) [0] 「禁止叛乱(对主权者的基本权利的一切反抗都是叛乱)的世俗法,作为世俗法而言,要不是根据禁止背信弃义的自然法,是不具有任何拘束力的。(Leviathan Ch.30)」 [1] 与Jean Hampton的解释类似的还有阿伦特的解释,可见汉娜·阿伦特(2008),《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 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pp.203-209;(2007),《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pp.36-37、56、140。 [2] 我觉得得不出更强的结论。这一点构成了霍布斯与洛克的重要分别。洛克相信自然状态,或前国家的人,可以通过诉诸先天自然法而达成某种关于道德秩序的共识,但霍布斯不相信这一点,他反而相信,人们都会认为自己是理性的,并且争论不休。「人的自然:人总相信他们自己比别人更聪明。谁也无法阻止这些分歧的出现。(De Cive Ch.6 注释2)」 [3] 但是不能因为预见到自己会被伤害而提前抵抗,见Leviathan Ch.27引文后文。此外,私人判断一直在进行,但是是否有权利这一道德地位是不一定的。并且,不知为何,霍布斯相信人们会做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利做的事,一件事有没有权利去做对他们很重要。 [4] 这一工作我们将在下面进行。 [5] Raz, Joseph. Practical Reason and Nor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6] H. L. A. Hart 「Commands and Authoritative Legal Reasons "in Authority: Reading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ed. Joseph Raz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0], 93 [7] 「尽管说起某次大规模的反叛时常常是说某个国家的人民拿起了武器,其实,真正反叛的只是那些实际拿起武器的人或与他们勾结在一起的人。(De Cive 6.1)」 [8] Cf. De Cive 6.2, Leviathan Ch.42 [9] Lloyd, S. A. (1992) Ideals as Interests in Hobbes’s Leviathan; Peter J. Steinberger,Hobbesian Resista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6, no. 4 (2002), 856–865. Michael Davis,「Heavenly Philosophy: What Thomas Hobbes said to Jean Hampton,」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32, no. 3 (2006), 341–364. [10] 「但如果有一大群人已经不义地反抗了主权者或犯了死罪、人人自知必将因此而丧生,那么这时他们是不是有自由联合起来互相协助、互相防卫呢?当然有,因为他们只是保卫自己的生命,这一点不论有罪没罪的人都同样可以做。他们当初破坏义务时诚然是不义的,往后拿起武器时虽然是支持他们已经做出的行为,但却不是一种新的不义行为了。如果他们只是为了保卫人身,便根本不是不义的行为。但颁布赦令后,就使蒙赦者不得再以自卫为口实,并使他们继续帮助或保卫他人成为不合法的行为。」 Leviathan Ch.21 [11] 「对于他说来,有自由服从的时候就是他的生命处于敌人看守和防卫范围以内的时候。因为这时他已经不再得到原有主权者的保护,而只凭自己的贡献受到敌人的保护……但一个人如果除开臣民的义务以外还承担了一种新的士兵的义务,那么当原有权力当局还在继续战斗并在其军队或守备队中发给给养时,他就没有臣服于一个新的权力当局的自由,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能埋怨说,没有得到保护和没有得到当兵的生计。不过,当这一些也失去了的时候,一个士兵便也可以向他感到最有希望的方面去求得保护,并可以合法地臣服于他的新主人。」Leviathan 综述与结论 [12] 「被俘入监或以镣铐拘禁的人虽然被制服了,但却没有被征服;因为他还是一个敌人,而且可以在办得到的时候挽救自己。」Leviathan 综述与结论「不是指关在牢狱中或用刑具锁押起来、等待俘获他的主人或从俘获者那里购买他的主人考虑怎样处理的那种俘虏。因为这种人一般都称为奴隶,根本不受什么义务约束;他可以打开镣铐或监狱,杀死或虏走他的主人;这样做是合乎正义的。而臣仆所指的是一个被俘获后如果已经让他获得人身自由,而且允诺不再逃跑,也不对主人使用暴力,从而得到了主人信赖的人。因此,对于被征服者的管辖权便不是由战胜而来的,乃是由于他自己的信约而来的。他之所以被拘束,也不是由于被征服;也就是说,他并不因为被打败、被抓住或被打得奔逃溃窜就负有义务,而只是因为他迁就并服从了战胜者。战胜者在没有允诺赦生前也不因为敌人投降就有义务让敌人可以免于听凭自己任意处理。投降一事只在战胜者任其自己考虑认为适宜时才有约束力。当人们要求所谓的饶命时,便是通过投降来避免战胜者眼前的愤怒,然后再以赎金或服役来和议求生。因此,获得饶命的人并没有免死,而只是延缓杀戮,以待将来考虑。因为这并不是以保全生命为条件的投降,而是任其处理的投降。唯有当战胜者给他人身自由之时,他的生命才得到了保障,他的服役也才成了应分之事。因为在监狱里或带着镣铐干活的奴隶,不是由于负有义务而干活,乃是由于要避免俘获他的主义的残酷待遇。」Leviathan Ch.20 [13] 「如果一个国王在战争中被征服,自己臣服于战胜者,他的臣民就解除了原先的义务,而对战胜者担负义务。但如果他是被俘或没有获得人身自由,就不应当认为他放弃了主权,于是臣民也就有义务要服从原先派任的官员;这些官员不是以他们本身的名义,而是以国王的名义进行统治的。」Leviathan Ch.21 [14] 虽然我们认为Sreedhar对「契约合同的不可能」的回应是失败的,但是我们认为,「契约合同的不可能」完全可以还原到「审慎理性的不可能」,因为「有无权利更换主权者」或「有无权利在国家之下结盟」的根本基础依然是「理性」的评估。所以如果「审慎理性的不可能」可以被回应,我们就可以论证成功一种叛乱权。 [15] 类似的表述,可见 Leviathan Ch.21, Ch.46 "冒犯人民的事情不是别的,乃是统治他们的方式不是每一个人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而是公众的代表(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会议)认为合适的方式,也就是受到一个独断政府的统治。由于这一点,他们咒骂他们的上级。也许要到经受内战以后不久,他们才会认识到没有这种独断的政府,这种战争就会永远持续下去;并且认识到,使法律具有力量和权威的不是空谈和允诺,而是人和武力。",A.E. in Behemoth,如「那些罗马教会宣扬的教义,其中残留着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人的意味不明的学说,而这些哲学学说不仅本与宗教无甚关联,而且只会滋生不满、不和,并最终导致叛乱和内战」「 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在青年时代阅读过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的著名人物所写的关于他们的政体和伟大事迹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民主政府被冠以「自由」的光荣名称而受到赞誉,而君主制则被诬蔑为『暴政』。」, etc. [16] 但是这并不是在重复谴责霍布斯是极权主义者的陈词滥调。无法避免暴政的理论很多,它们并非都是极权主义理论,霍布斯的主权者也并非不需要遵守任何规范性要求。 [17] Watkins, John W. N. (1973). Hobbes's System of Ideas: A Study in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Philosophical Theories. Hutchinson. pp.127 [18] 当然,这句话看上去更像一句修辞,因为在霍布斯的意义上的正确哲学不可能是一种不支持和平的哲学,而假如正确的哲学家真得批评主权者,比如在主权者放弃那些国家存在必要的权力的案例中,主权者是违背了自然法而丧失了权利的。 [19] 此外,还有一种较小的可能性,即人的身体结构发生了某种变化,使得这个国家中,许多人的身体中有朝向比如共和主义自由的endeavor,而反思性的评估,进行叛乱带来的政治上的整体对自我保全的好处,是超过一段时间的不和平带来的自我保全的损害(比如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身体结构),那么这种叛乱就必须被理性赋予「权利」这一道德地位。Sreedhar认为只有基于自我保全的叛乱,「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式的叛乱才可能是正当的叛乱,而基于意识形态的叛乱则不会是正当的,但正如上述,我们认为这种正当叛乱也是可能的(不过这种叛乱权要求一种不同于霍布斯式的人性,而正文中对叛乱权的辩护依然是基于霍布斯式的人性)。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Philosophia 哲学社
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备战深国交网”除发布相关深国交原创文章内容外,致力于分享国际生优秀学习干货文章。如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原谅,并联系微信547840900(备战深国交)进行处理。另外,备考深国交,了解深国交及计划参与深国交项目合作均可添加QQ/微信:547840900(加好友时请标明身份否则极有可能加不上),转载请保留出处和链接!
非常欢迎品牌的推广以及战略合作,请将您的合作方案发邮件至v@scieok.cn本文链接:http://www.scieok.cn/post/2529.html
-
<< 上一篇 下一篇 >>
一种霍布斯式的叛乱权是可能的吗?/ 原创(下)
21120 人参与 2021年11月13日 18:55 分类 : 深国交哲学社 评论
search zhannei
深国交2024年英美本科录取小计
-

未标注”原创“的文章均转载自于网络上公开信息,原创不易,转载请标明出处
深国交备考 |
如何备考深国交 |
深国交考试 |
深国交培训机构 |
备战深国交 |
联系方式
Copyright www.ScieOk.cn Some Rights Reserved.网站备案号:京ICP备19023092号-1商务合作
友情链接:X-Rights.org |中国校园反性骚扰组织 | 留学百词斩 | 南非好望角芦荟胶 | 云南教师招聘考试网 | 备战韦尔斯利网| 备战Wellesley